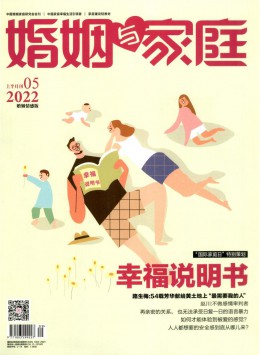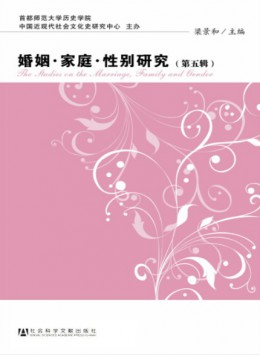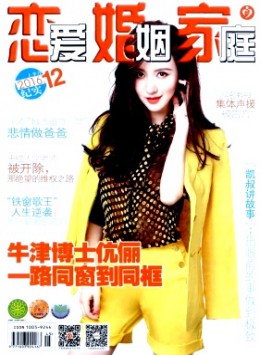婚姻家庭合同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婚姻家庭合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關鍵詞] 沖突法婚姻家庭立法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China’s Legislation of Conflicts Law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Zhang Ling
(International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Law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opted on October 28, 2010,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and gained development in several aspects, a real milestone in the Chines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s far as the legisl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international marriage and family is concerned, the improvements are mainly as follows: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regulating object; more flexibility added to conflict rules; the doctrine of the autonomy of the parties demonstrating respect for and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 of the weak which declares the pursuit of substantive justice inherent in conflicts law.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交往的不斷發展,人員跨國流動日益頻繁,涉外婚姻家庭領域的糾紛也越來越多,《民法通則》、《收養法》以及有關行政法規、司法解釋對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的規定已不足以適應實踐發展的需要。主要體現于以下兩大方面:第一,并非所有涉外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適用都能在上述法律規定中找到依據;第二,就已經規定的法律適用規范而言,尚存在不完整、不合理、不科學的情況。2010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以下簡稱“《法律適用法》”)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以往我國沖突法立法不系統、不全面的狀況,結合國際上國際私法新發展與中國實際,對原有法律規定中不合理、不科學的規定予以修改。在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立法上,該法設專章對結婚、夫妻關系、父母子女關系、離婚、收養、扶養、監護關系的法律適用做出規定,調整對象的范圍更為廣泛、全面。同時,在具體規則內容設計上,該法順應國際私法與婚姻家庭實體法的發展趨勢、充分吸收與借鑒國際上先進立法經驗,對原有僵硬的沖突規范予以矯正,力圖實現法律選擇的靈活與公正;首次在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選擇問題上引入有限的意思自治原則,彰顯了沖突法對私權的尊重與保護;第一次在立法上確認保護弱者利益原則在父母子女、扶養與監護關系法律選擇中的適用,申明了沖突法對實質正義價值目標的追求。由此可見,在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立法上,《法律適用法》在諸多方面有所突破與發展。本文側重從新舊對比角度,探究我國婚姻家庭沖突法立法的新發展。
一、《法律適用法》對涉外婚姻家庭關系調整范圍的拓展
婚姻家庭沖突法調整對象的范圍應與實體法規定大致匹配,因此,在涉外婚姻家庭領域,沖突法至少應當覆蓋涉外結婚、離婚、夫妻關系、父母子女關系、扶養、監護與收養關系等基本問題。隨著婚姻實體法的發展,沖突法的調整范圍還可能進一步擴大。
在《法律適用法》通過之前,《民法通則》、《收養法》及其司法解釋以及有關行政法規對涉外結婚、離婚、扶養、監護、收養的法律適用問題有所調整,但仍存在法律尚未觸及的空白區域。一方面,上述法律規定沒有對涉外婚姻家庭關系中夫妻關系與父母子女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做出專門規定,另一方面,由于當時我國涉外民事交往尚不發達,處理相關法律糾紛的經驗比較有限,上述法律規定調整的對象往往只局限于某類涉外婚姻家庭關系中的某種情形。例如,《民法通則》第147條有關涉外結婚法律適用的規定僅限于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外國人結婚的情況。而兩個中國公民在國外締結婚姻、外國人之間在我國締結婚姻以及外國人之間在外國締結婚姻要求我國承認其效力的情況就不在《民法通則》調整范圍之內。盡管有關行政機對來華工作的外國人之間在中國境內登記結婚、華僑、出國人員在境外結婚以及居住于駐在國的我國公民在駐外使領館登記結婚的問題頒布了相應的行政法規,但這些規定也并非能夠完全彌補《民法通則》調整范圍的缺失。類似的情況在涉外離婚、收養關系法律適用的規定中也有出現。這種做法最明顯的弊端是對沒有規定的涉外民事關系,其法律適用缺乏法律依據,并且,就具有更高位階的“法律”而言,調整范圍的缺失也容易帶來實踐不統一的消極后果。這種立法狀況已經不能適應與滿足我國對外交往的現狀與需求,據此,《法律適用法》在婚姻家庭沖突法立法過程中對調整對象的范圍進行了拓展:一方面在原有立法基礎上補充涉外夫妻關系與父母子女關系法律適用的規定,另一方面,在某一具體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的規定上不再列舉具體情形,彌補了以往法律規定范圍缺失的局限。
二、沖突規范的適度“軟化”:沖突法立法對靈活性與確定性的兼顧
沖突法本身不涉及任何實體內容,也不直接調整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但它與實體法一樣,都負有公平與公正解決爭議的責任。美國沖突法革命對世界國際私法立法的最大貢獻之一就在于引發了人們對法律選擇結果合理性的關注。盡管大多數國家并沒有選擇徹底拋棄沖突規則的激進路徑,但在沖突法制定過程中對傳統沖突規范進行“軟化”處理,通過增強法律選擇的靈活性實現對結果公正的追求已經得到普遍認同。在軟化沖突規范的過程中,如何防止“靈活性”對“確定性”的沖擊,在最大限度內實現二者的平衡也成為立法者考量的重要因素。這種立法特點在《法律適用法》中也有所體現,在婚姻家庭領域,突出表現于以下三方面:
(一)分割方法的采用
對同類法律關系依據其性質不同進行分割,分別制定不同的沖突規范,這在婚姻家庭沖突法立法中是比較常見的做法,諸如將結婚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夫妻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進行區分的做法在各國沖突法立法中已經很普遍。在《法律適用法》通過之前,我國婚姻家庭沖突法立法沒有采用分割方法,忽略了同類法律關系中不同問題的特性,相對應的立法規定也比較僵硬。為克服原有沖突規范的僵化,《法律適用法》在婚姻家庭領域比較廣泛的采用分割方法,主要表現于以下四方面:第一,在涉外結婚法律適用規定上,將結婚的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相區分,前者更加強調當事人共同屬人法(特別是共同經常居所地法)的優先適用,后者則采用選擇性沖突規范盡量維護婚姻形式的有效性。第二,在涉外離婚法律選擇上,將訴訟離婚與協議離婚相區分,前者固守原有的法院地法規則,后者允許意思自治原則與當事人屬人法的適用;第三,在涉外夫妻關系法律適用方面,將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進行區分,在夫妻財產關系法律適用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則。第四,在涉外收養法律適用問題上,根據收養中不同法律關系的特點將其分為收養的條件和手續、收養的效力以及收養關系的解除分別制定不同的沖突規范。相對于以往立法,上述分割方法的采用體現出我國沖突法立法對某類婚姻家庭關系中不同問題特質的關注以及對法律選擇結果合理性的追求。
(二)選擇性沖突規范的運用
選擇性沖突規范通過增加連結點的數量提高法律選擇的靈活性,從而實現沖突法對結果公正的追求,其價值在沖突法立法中獲得普遍認同。《法律適用法》在婚姻家庭領域也大量采用此種類型的沖突規范,具體表現于兩種適用模式:一是有條件選擇性沖突規范的運用。立法一方面規定了若干可供選擇的連結點,另一方面又結合具體法律關系的特點規定了明確的選法順序,相對于單一連結點的適用,增加了法律選擇的靈活性,同時也基本保證法律選擇的確定性。此種類型沖突規范的運用比較廣泛,在結婚實質要件、夫妻關系、父母子女關系、協議離婚的法律選擇問題上都有所適用。二是并不明確規定連結點適用的順序,而是通過提供選法導向促進某種實體結果的實現。例如,為促進婚姻形式的有效,該法第22條規定:“結婚手續,符合婚姻締結地法律、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的,均為有效。”據此,只要符合上述任一連結點所在國法律關于結婚形式要件的規定,該婚姻在形式上即為有效,表現出沖突法對婚姻實體法尊重當事人合意,崇尚婚姻自由的響應。在涉外父母子女、扶養、監護關系法律適用問題上,該法在規定復數連結點的同時,提供了進一步選法的原則,彰顯出婚姻家庭法對弱者利益保護的特別關注。應當說,此種“軟化”的立法技術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實現法律選擇對實體結果的追求,當然,沖突規范內部蘊含的“有利原則”對結果的明確導向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沖突規范軟化后對確定性的沖擊。
由此可見,《法律適用法》在婚姻家庭法律適用立法中雖然大量采用選擇性沖突規范意圖增強法律選擇的靈活性、實現其結果的合理與公正,但在克服以往立法僵化性弱點的同時,也在竭力避免法官確定準據法的任意性。
(三)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為補缺
涉外民事關系應當適用與其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作為準據法,這是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的基本規則。但在如何確定最密切聯系法律問題上,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曾經存在比較大的分歧。以美國沖突法革命為代表,一些普通法系國家曾竭力反對將沖突法成文化,主張拋棄僵化的沖突規范,以最密切聯系原則為法律選擇的基本方法,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分析考慮與爭議相關的各種因素確定涉外民事爭議應當適用的法律。應當承認,相對于傳統的沖突法規則,最密切聯系原則為司法實踐提供了一種靈活的法律選擇方法,適應了涉外民事關系的復雜性,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因沖突規則的剛性與僵化導致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審理結果。但另一方面,最密切聯系原則在依賴法官自由裁量權實現法律選擇靈活性優勢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陷入法律適用不確定性與不可預見性的困境。無限度、無標準的最密切聯系原則在實踐中適用的結果很可能背離其追求公平、合理的初始目標。因此,各國沖突法立法在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時通常予以限制。
《法律適用法》第2條將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法律未作規定的補缺規則,一方面肯定該原則在解決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中的積極意義,允許采用一種靈活的、富有彈性的法律選擇方法確定準據法,實現法律適用結果的公平與合理,另一方面又對該原則的適用范圍加以限定,防止其過度適用對法律選擇確定性、可預見性與公正性帶來風險。該條在涉外婚姻家庭領域也存在適用空間。例如,在夫妻人身關系的法律適用上,如果當事人沒有共同經常居所,也沒有共同國籍,就需要適用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準據法。依次類推,在結婚的實質要件、夫妻財產關系、收養關系解除的法律適用中,最密切聯系原則都可能發揮其補缺的功能。
三、有限意思自治原則的適用:沖突法立法對私權的尊重與保護
意思自治作為沖突法的一項重要的法律選擇規則不但在涉外合同法律適用中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可與接受,并且正逐步向侵權、婚姻家庭、繼承等領域滲透。《法律適用法》在夫妻財產關系與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上引入意思自治原則,并且將其作為首要規則予以適用是我國沖突法立法在婚姻家庭領域的一大突破。
(一)意思自治原則向婚姻家庭領域的擴張
私法自治理念的普及讓人們逐漸接受只有在最大限度內承認私人的意志,才能實現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國家只在私人行為涉及國家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時才有介入的必要,因此,任何私法部門或領域,在其享有私法自治的程度和范圍內,都應允許意思自治方法發揮作用。對私權的尊重與保護已經滲透到婚姻家庭領域,隨著社會經濟與文明的發展,各國婚姻家庭實體法傾向于給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留有一定空間。大多數國家允許夫妻雙方以合法約定的方式,決定婚前或婚后財產的歸屬等婚姻財產關系問題,對雙方當事人通過協議解除婚姻關系的限制越來越少。與此相對應,如果上述法律關系存在涉外因素,而與其相關聯國家的法律規定有所不同,沖突法也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不損害善意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允許夫妻雙方自主選擇適用于其財產關系以及解除其婚姻關系的法律。這既是對實體法維護私法自治的呼應,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沖突法對當事人合理預期的保護。
在我國婚姻家庭實體法修訂過程中,對私權的尊重與保護一直是其立法完善的主脈絡,無論在夫妻財產制度上從單一的法定共同財產制到法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并立的發展,還是在離婚問題上從需要提交單位介紹信到對協議離婚實質審查的取消,都彰顯出實體法對婚姻當事人自主決定其財產狀況與解除婚姻關系自由權利的尊重。實體法的發展為意思自治原則向我國婚姻家庭沖突法的拓展提供了立法與實踐依據,在夫妻財產問題以及婚姻雙方當事人自愿解除婚姻關系的情況下,應當允許他們在法律適用問題上行使自治權。
(二)對婚姻家庭領域意思自治原則的適用予以限制
應當承認,相對于涉外合同法律關系而言,夫妻財產爭議不是單純的財產關系,協議離婚也不等同于契約關系的解除,它們與當事人身份關系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不可避免地牽涉到各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觀念、與社會公共利益等因素。因此,當事人在該領域行使意思自治的權利也必然受到限制,這種限制主要表現于當事人合意選擇的法律與夫妻雙方以及所涉法律關系應當存在實質性聯系。因此,《法律適用法》在夫妻財產關系法律適用規定上將當事人意思自治選法的范圍限定于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者主要財產所在地法律;而對于協議離婚,只允許當事人在其中一方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范圍內作出選擇。這種限制也符合婚姻家庭關系尋求穩定與可預見的特點,具有合理性。
四、保護弱者利益原則的引入:沖突法立法對實質正義價值目標的訴求
世界范圍內人權保護運動的蓬勃興起極大地影響與推動法律的改革與發展,各國在實體法立法過程中開始關注對主體間實質平等價值的追求。反映在國際私法領域,突出表現于通過沖突規范實現對弱者利益的保護,這種立法趨勢在20世紀后期愈發明顯。實際上,保護弱者原則在國際私法上的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美國沖突法革命思潮中卡弗斯的結果選擇說。卡弗斯竭力反對傳統法律選擇規則僅關注空間意義上選法的適當性,而忽略所選法律的內容及其適用于具體案件的結果是否公正。他質疑如果對法律選擇將會怎樣影響案件糾紛的問題置之不顧,法院解決糾紛的職責將如何實現?因此提出法院在法律選擇方面,不應是消極、被動的,而必須去考察相互沖突的法律規則的具體內容,比較適用不同法律所導致的結果,并衡量這種結果對當事人是否公正。結果選擇說對實體結果公正的關注再次引發了人們對國際私法價值目標如何在“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間進行平衡的思考。從國際私法立法發展現狀來看,對實質正義的追求已經融入到各國法律選擇規則之中,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當涉外民事糾紛雙方當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生活能力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時,通過結果定向的沖突規則實現對弱者利益的保護。這是國際私法在現代社會經濟條件下對傳統價值目標的一種超越。
在婚姻家庭領域,婦女、兒童、老人、被扶養人、被監護人通常處于弱勢地位,立法者如果只考慮過程的正當, 忽略年齡、生理、勞動能力、經濟條件等差別而導致的個體差異,形式上的平等很可能掩蓋實質上的不平等。對實質正義的追求在我國婚姻家庭實體法的發展變遷中已有明顯表現:在確保所有婚姻家庭關系主體都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基礎上,無論對扶養范圍的擴大,還是離婚救濟制度的建立,都表明立法者在踐行形式正義理念的基礎上, 通過保護婚姻家庭中弱勢群體, 對實質正義的伸張。與此相呼應,《法律適用法》首次在父母子女關系、扶養與監護關系的法律適用上采用保護弱者利益原則,充分體現了我國沖突法立法對實質正義價值目標的訴求。具體而言,在父母子女沒有共同經常居所的情況下,應當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國籍國法律中有利于保護弱者權益的法律,體現了立法者對年幼子女與年邁老人利益保護的特別關注;在扶養和監護的法律適用上,以保護弱者利益原則取代最密切聯系原則作為選擇準據法的思路,則凸顯出對處于弱勢的被扶養人與被監護人利益保護的傾向。
關乎婚姻家庭的法律深深觸及一國特有的道德、宗教和社會生活基本原則的靈魂,通常被認為是有關公共政策的法律問題。實體法在這一領域的沖突必然激烈并難以調和,因此,沖突法在解決涉外婚姻家庭糾紛中將長期發揮重要作用。《法律適用法》在婚姻家庭領域進行比較全面與深入的改革,對合理解決涉外婚姻家庭爭議、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促進國際民事交往將產生積極意義。同時需要指出,立法的變革對司法實踐的發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在屬人法連結點改革后,相應出現對涉外婚姻家庭糾紛中當事人經常居所地的確定問題;意思自治原則在夫妻財產關系法律選擇中的采用附帶產生如何保護第三方債權人權利的問題;保護弱者原則的適用需要考慮如何防范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以及合理考慮扶養人、監護人經濟與實際擔負能力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待司法實踐進一步嘗試與探索。
[參考文獻]
[1] 李良才:《荷蘭同性婚姻的國際私法問題》[J],載《蘭州學刊》2010年第7期。
[2]鄒國勇譯注:《外國國際私法立法精選》[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118、119、151、155、156頁。
[3] 宋曉:《當代國際私法的實體取向》[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頁。
[4] [美]西蒙尼德斯:《20世紀末的國際私法——進步還是后退?》[C],宋曉譯,黃進校,載《民商法論叢》,2002年第3號(總第24卷),第404頁。
[5] 張翔宇著:《現代美國國際私法學說研究》[M],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頁。
第2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Abstract: Perfecting moral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of divorce,it is necessary to clear right of spouse in “marriage law”,as well as the scope of identity right,we should consider four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uses and judicial practice,firstly,the duration of marriage,and the victims contribution to the spouse or family;secondly,infringement reason of the infringer,subjective motives,the degree of fault and specific circumstances;thirdly,the extent and consequences of non-property damage of victims and impact of post-divorce life;fourthly,loc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capacity of compensation obligors.
關鍵詞: 配偶權;離婚損害;精神損害賠償
Key words: right of spouse;divorce damage;compensation for mental loss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0-0246-02
0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下稱《婚姻法》)第四十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下稱《解釋(一)》)第二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有關規定確立了我國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但現有法律規定不具體、賠償范圍狹窄等立法缺陷,使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存在不足,筆者試從《婚姻法》保護配偶權的本質出發,對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主體、賠償義務主體、賠償范圍和賠償數額、適用程序、民事責任方式等問題談一些看法。
1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主體
配偶權在我國是一項有爭議的權利,理論界對配偶權是什么,還沒有最終的定論,但是隨著《婚姻法》和《解釋(一)》的出臺,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離婚案件中基于配偶權由過錯方對無過錯方進行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例越來越多。由此筆者認為,配偶權這種因男女合法結婚而形成的客觀權利,與離婚精神損害之間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系,要完善我國的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就必須在《婚姻法》中明確規定配偶權。結合《婚姻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給離婚精神損害下個定義,即離婚精神損害是指合法夫妻因一方重大過錯離婚時,無過錯方因對方過錯行為而受到的非財產上損害。這里,非財產上損害,指不表現為財產上損毀的精神痛苦和肉體痛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精神損害”。這種非財產上損害其實質就是過錯方的侵權行為對另一方配偶權的侵害,并因配偶權的侵害給無過錯方造成了較嚴重的精神痛苦和肉體痛苦。
2賠償義務主體
在理論上,配偶權的絕對權性質決定了配偶以外的任何人都是配偶權的義務主體,都負有不得侵害配偶權的義務,若第三者侵害了合法婚姻關系中無過錯方的配偶權,受害人應有權向其主張損害賠償。楊立新教授認為,“在重婚和與他人同居的侵害配偶權的損害賠償關系中,是完全可以向重婚和同居的對方請求損害賠償的,因為他們是這一侵權行為的共同加害人,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有責任賠償受害人的損失。”但是,《解釋(一)》對法律規定不明的條文作出了不恰當的限制性解釋,制約了離婚損害賠償制度功效的發揮,導致了我國婚姻法缺乏對第三者破壞他人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規定,司法實踐中對第三者參與破壞他人家庭的行為明顯處罰不力。因此,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同居、通奸等故意侵害合法婚姻關系的第三者納入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義務主體范圍之內,對通過立法保護正常、和諧的婚姻家庭關系不受非法干涉,并使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賠償主體上趨以完備具有重大意義。
《婚姻法》第四十六條實際上規定了離因損害,司法實踐中對因離婚對弱者造成的損害,因法律無明文規定,一般采取分割財產時對弱者適當照顧的原則進行救濟。筆者認為,為維護婚姻關系的穩定,保護婚姻家庭中弱者的權益,將來修改《婚姻法》或出臺新的司法解釋對提起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情形進行明確時,都應從離因損害和離婚損害兩個方面進行考慮。
從構成離婚損害的角度來分析,離婚本身應成為受害方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定情形,這體現了法律對弱者的保護。婚姻的本質是一種契約,是男女雙方為了永久相伴生活并負起婚姻家庭的社會責任,在自愿平等的基礎上達成的協議,結婚證書是這種協議的法定書面形式。就此而言,婚姻作為合同或相當于合同,一方提出離婚(無論理由、目的是什么可看做是合同一方毀約),經法院或相關部門調解無效,導致婚姻家庭解體的,正常履行婚姻義務的配偶方自然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有學者認為,這種精神損害,依侵權行為理論解釋,在法的構成上,尚屬不足,如果解釋為救濟因離婚所產生的損害而設定的法律保護政策較為妥當。建議《婚姻法》規定離婚本身成為受害方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法定情形的法律依據。如上文所述,在親屬法中配偶關系是血親、姻親得以產生的基礎,離婚事實的產生受到損害的受害方,不僅是婚姻合同中的另一方配偶,還包括合同受益人,即配偶的子女和與配偶雙方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父母,從發揮家庭的社會功能來講,把離婚本身作為受害方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定情形,有利于保護婚姻家庭中弱者的利益,建議《婚姻法》規定離婚本身成為受害方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法定情形的現實依據。
3賠償范圍
離因精神損害賠償保護的是離婚案件中受害方因過錯方侵權造成的非財產上損害,法律應從符合侵權行為構要件的離婚原因中,選擇對婚姻關系危害較嚴重的情形,將其規定為離因侵權行為。
3.1 配偶不為婚外性生活,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本質要求,是夫妻忠實義務的具體體現,夫妻性生活的排他性決定了婚外是影響婚姻關系穩定的首要因素。《婚姻法》規定的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是婚外的表現,現實中婚外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因各種婚外導致婚姻解體的案例也是舉不勝舉。隨著國門打開西風東進,西方性解放思想使婚外愈演愈烈,對婚姻家庭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破壞也日益嚴重。
3.2 賭博、吸毒兩大惡習不僅是違法行為,如長期為之,并不亞于實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給另一方造成的傷害,《婚姻法》規定為離婚的理由,卻沒有規定可以提出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其他危害家庭不良行為是指四種行為以外危害家庭生活造成婚姻關系破裂的行為,如“網絡婚姻”,當網絡的普及給人們帶來方便的同時,也成了人們婚外情感交流的工具,有人在網上養“情人”、有人在網上“結婚生子”,因網戀引起的離婚訴訟從無到有日趨多見,作為“精神外遇”的網戀,影響了配偶之間感情的交流,已經成為婚姻解體的新殺手。
3.3 將侵害配偶生育權作為提起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情形之一,是基于以下考慮:第一,侵害配偶生育權的行為在現實中客觀存在,如一離婚案件中,丈夫代某因妻子唐某擅自墮胎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5000元,理由是妻子唐某無正當理由,未經丈夫代某同意擅自將符合法律規定的胎兒引產的行為,侵害了代某作為丈夫的生育權;第二,侵害配偶生育權具有潛在的危害性,根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規定,一對夫婦終生只能生育一個孩子,故意侵害配偶生育權,當配偶已不能生育或離婚后不能再婚時,就會導致侵權后果的產生;第三,第三人也能對配偶生育權造成侵害,如妻子因與他人通奸而懷孕生子,第三人的通奸行為不僅侵害了丈夫對妻子的性權利也侵害了丈夫合法的生育權。
3.4 婚姻當事人,不履行法律規定或社會習慣認可的婚姻家庭義務,經親友或有關單位說服教育,仍不履行,對家庭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以認定為不承擔家庭義務。配偶權中的大部分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一方不承擔同居義務、生育義務、監護子女義務、扶養扶助義務,實質上是以不作為的方式侵害了對方的配偶權,違背了婚姻家庭的本意,因上述原因產生嚴重后果當事人要求離婚,受害方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律應明確加以保護。
4賠償數額應考慮的因素
根據《婚姻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結合婚姻關系的實質內容,認為確定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應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4.1 結婚時間雙方結婚時間的長短,受害人對配偶或家庭的貢獻不一樣。婚姻的本質是男女共同生活、共同承擔一定的家庭責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雙方都會對另一方和家庭進行感情和經濟上的投入,承擔相應的家務勞動,因此,結婚一個月離婚和結婚幾年、幾十年離婚,使當事人受到的損害也是明顯不同的。現實生活中,夫妻一方特別是女方,承擔了大量或全部的家務勞動,把全部精力和青春奉獻給了配偶和家庭,她(他)們從另一方面對家庭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筆者認為,結婚時間長和對家庭貢獻較大的,賠償數額相對要高。
4.2 侵權情況侵權人的侵權原因、主觀動機、過錯程度和具體情節,是確定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決定性因素。侵權原因主要看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發生有沒有責任,因受害人引起的一方侵權行為發生,賠償數額相應減少。侵權行為的手段、方式、場合、持續的時間等具體情節的不同,反映了侵權行為社會危害程度的不同,在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上理應有所反映。
4.3 損害后果過錯方對受害人非財產上損害的程度和后果對受害人離婚后生活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是確定賠償數額的重要依據。一方面,受害人因對方的侵權行為,生理上、心理上受傷害較重,離婚后社會評價降低再婚比較困難、無生活來源的,賠償數額要高;另一方面,侵權人的侵權行為并未造成嚴重危害的,賠償數額不宜過高。
4.4 經濟因素主要考慮當地的經濟狀況和賠償義務人的經濟能力。一要按照當地的生活水準合情合理的確定賠償數額。二要對侵權人的經濟能力也要有所考慮即要能撫慰受害人又能達到懲治過錯方的目的。
5賠償適用程序
關于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程序,新《婚姻法》未作出規定。筆者認為既可適用行政離婚登記程序,亦可適用民事離婚訴訟程序。因為,民法屬于私法,在夫妻雙方就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已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夫妻雙方又同意通過行政登記離婚,法律應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不予干預。如果當事人達不成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協議,則可通過訴訟離婚,由人民法院依法判決。
6賠償的責任形式
至于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國外的立法,大多規定了撫慰金制度。離婚精神損害賠償,重在慰撫受害人的精神創傷,建議在制定民法典時,在民事責任中增設撫慰金制度。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侵害名譽權等人格權的民事責任包括停止侵害、賠禮道歉等非財產責任和賠償損失的財產責任兩種方式。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形式,也可適用非財產責任和財產責任兩種方式。過錯配偶的違法行為造成無過錯配偶的精神創傷的,可以請求給付撫慰金。無過錯配偶的名譽權等如受損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等形式。
參考文獻:
[1]楊立新著.新版精神損害賠償.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第3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關鍵詞:夫妻共同債務;價值理念;家庭共同生活;制度設計
中圖分類號:df5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04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人們之間商品交易和物質往來趨于頻繁,夫妻在婚姻存續期間因日常生產、生活需要,亦無可避免地與第三人產生債權債務關系,而且漸由純粹的生活性債權債務關系向經營性債權債務關系轉化。然在夫妻一方或雙方為債務人之場合,此債務定性如何,是夫妻共同債務抑或個人債務,直接關涉保護夫妻非舉債方的個人利益和債權人的財產權益及交易安全問題。有鑒于此,本文以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為研究對象,對我國現行夫妻共同債務定性規則予以審思,并提出完善設想,以期在依法衡平保護夫妻非舉債方的利益和債權人合法權益的二元價值追求中,尋求一條科學合理的解決路徑。
一、立法審思: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解讀
我國有關夫妻共同債務之規定主要體現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中。從其規定看,對于夫妻共同債務之認定,采雙重標準。其一為所負債務目的論。即根據我國《婚姻法》第41條、《婚姻法解釋(二)》第23條之規定,審視所負債務是否為家庭共同生活之目的,若所負債務確為家庭共同利益,則無論婚前或婚后所負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其二為所負債務推定論。即根據《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之規定,在夫妻一方名義舉債之情形下,不論舉債目的如何,只要此債務發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除夫妻另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能證明債權人知道夫妻雙方實行分別財產制之外,應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從其內容看,上述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雙重標準存在邏輯沖突。即“推定論”忽略了夫妻單方舉債可能存在并不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形,卻將此情形統一認定為共同債務,這恰與“目的論”主張所負債務必須用于共同生活才能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標準相沖突,易造成實務中法律適用混亂,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如有的案件直接援用《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而有的案件則援用《婚姻法》第41條及《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意見》第17條之規定,做出相反認定[1]。這將嚴重損害夫妻非舉債方及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更難以彰顯法之公平價值。
筆者認為,我國夫妻共同債務在性質認定上之所以存在雙重標準,歸根結底在于立法并未澄清正確理念,制定規則時價值取向存在一定誤區和偏差,未能以維護婚姻家庭利益及社會利益有機統一的根本原則為指針,全面、綜合地考量實際情況,僅根據不同情況制定不同規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樣,難以徹底解決實踐中紛繁復雜的夫妻債務類型。惟可行之處在于,對我國現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進行反思,對其立法理念予以澄清,從立法體例及內容層面綜合考量,制定系統的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破解實務中因適用不同認定規則而有礙公平的司法困境。
二、理念澄清:從價值取舍到價值整合
(一)價值取舍:兩種立法理念的博弈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而婚姻則是構成家庭的緊密紐帶。建國以來,我國十分重視婚姻家庭立法,先后頒布了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并于2001年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婚姻家庭新情況對1980年《婚姻法》作了進一步修正。同時為有效解決司法實踐中出現的紛繁復雜的婚姻家庭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又適時出臺相關司法解釋,現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便構成了我國夫妻債務立法的重要淵源。從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規定的夫妻債務認定規則看,以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釋(二)》為分野,可分為兩個階段。此前立法對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均以所負債務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之目的為標準;而該司法解釋則對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采債務推定標準。此標準既出,即
改變了我國自1950年《婚姻法》既已確立的夫妻共同債務采共同生活目的論的認定標準,無形中擴大了夫妻共同債務的范圍。
筆者認為,《婚姻法解釋(二)》在夫妻債務認定規則上對《婚姻法》的細微變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立法對夫妻債務定性的不同態度及價值理念的改弦更張。《婚姻法》(含1950年、1980年、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主張以舉債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之目的作為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標準,體現了法注重維護婚姻共同體,保護婚姻當事人合法財產權益的價值理念。而《婚姻法解釋(二)》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上采債務推定原則,則體現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先保護債權人利益及市場交易安全的價值理念。上述二種立法理念反映出在大力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積極培育市民社會土壤的當下中國,立法在婚姻家庭利益與社會利益孰應優先保護的二難抉擇之間作出的價值取舍。然此種取舍卻割裂了婚姻家庭利益與社會利益需要同等保護的有機統一,使法的公平價值在利益衡量的天平之上左右搖擺,難以尋覓均衡的支點。
自1950年我國頒布首部《婚姻法》以來,婚姻法即以維護婚姻家庭穩定,保障家庭成員合法權益為理念,堅持夫妻共同債務認定以舉債用于共同生活為準則,將不為家庭共同生活所負之債務排除在共同債務之外。這不僅符合我國婚姻法倡導的家庭成員團結互助、共建幸福生活的立法精神,也有效地保護了夫妻非舉債方的財產利益,是法正義價值在家庭法領域的具體體現。然而,此立法理念卻忽視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和市場交易安全的保障,在這種理念之下,實務中曾有喪失誠信觀念的夫妻惡意串通,將實為共同債務卻狡辯為個人債務,然后假借離婚之名,將共同財產分割歸夫妻一方所有,債務卻歸另一方承擔,以此逃避債權人的追償,使交易安全缺乏應有之保障。有鑒于此,《婚姻法解釋(二)》有關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應運而生。不能否認,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在打擊夫妻惡意逃避債務,保障債權人利益及維護市場交易安全方面具有積極意義,然而我們更應當正視因此規則的推行而產生的另外一種事實,即離婚時,夫妻一方與第三人惡意串通,虛構債務,以此來侵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財產權益,使其正當利益在法的“庇護”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既有悖于法律的公正,也不利于夫妻另一方利益的保障及家庭乃至社會的穩定[2]。 由此可見,我國立法在夫妻債務認定規則的制定上所采的二種價值理念,無論作何取舍,都不能兼顧保護婚姻家庭利益及社會利益,使法陷入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筆者認為,我們應深刻認識到婚姻家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有機統一,市場經濟條件下二者需要給予同等對待和保護,因此應整合我國夫妻債務立法的價值理念,尋求婚姻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利益天平上的均衡支點,使二者相得益彰。
(二)價值整合:尋求婚姻家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和諧統一
在21世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家庭被時代賦予新的內涵,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家庭仍是傳統意義上人的物質及精神情感尋求慰藉和給足的集合,維護家庭穩定和保障家庭成員的利益是家庭的核心職能。另一方面家庭集合下的單個個體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涌動下,逐漸在市場交易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與社會利益角逐的浪潮中,家庭愈來愈被推到風口浪尖之上。法是權利和利益的表達,在家庭和社會之間,法不應偏廢其一,而是作為“中間人”和“調停者”,將二者的利益訴求表達在調和狀態,使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達致和諧統一。
夫妻債務立法理應如是。然從上文對我國夫妻債務立法的價值理念分析看,我國夫妻債務立法并未將婚姻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統籌兼顧,而是割裂開來,結果導致《婚姻法解釋(二)》中的債務認定規則與《婚姻法》相沖突,出現司法適用混亂的局面。筆者認為,在夫妻債務法領域,在具有家庭主體身份的夫妻和第三人之間,偏袒任何一方的利益均顯失公平。若依《婚姻法》之規定,雖有力地保護了婚姻當事人及家庭利益,但卻一定程度上損害債權人的財產權益及社會交易安全,若依《婚姻法解釋(二)》之規定,雖債權人財產權益及交易安全得以保障,但婚姻當事人及家庭利益卻遭致損害。因此應對夫妻債務立法將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進行取舍保護的不正確理念予以澄清,以統籌保護婚姻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為指導,對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予以修正和重構,使夫
非舉債方的財產權益和債權人的利益能夠得到衡平保護,使婚姻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夫妻債務法領域達致和諧統一的狀態。
三、夫妻共同債務:以“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論為依歸
如上文述,目前我國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有“目的論”和“推定論”兩種標準,“目的論”采實質主義,以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債務應為共同債務,“推定論”采形式主義,以凡發生在婚姻存續期間的債務除兩種情形外均應為共同債務。以夫妻債務立法所應秉持的立法理念檢視,此二種標準均不能兼顧保護夫妻非舉債方和債權人的財產權益。然從立法目的審視,在婚姻家庭領域立法應以保護婚姻家庭穩定、保障婚姻家庭當事人利益為宗旨,夫妻債務立法亦不例外。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論”過分保護債權人利益,容易誘發夫妻一方與第三人虛構債務的道德風險[3],不利于保護夫妻非舉債方利益和婚姻家庭利益,于婚姻家庭立法基本宗旨相悖違,應不為立法所取。夫妻共同債務“目的論”以債務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實際用途和目的出發,符合我國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宗旨,雖在規則設計上存在債權人因舉證不能而利益無以保障的漏洞,但可對規則予以改造,以使夫妻非舉債方和債權人利益能夠得到衡平保護,實現婚姻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和諧統一,因此,筆者主張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應以債務確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目的論”為依歸。
(一)以“家庭共同生活目的”為標準之正當性論析
夫妻共同債務之認定應以負債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目的”為標準,理由
在于:
第一,符合我國婚后所得共同財產制的立法精神。我國法定夫妻財產制采婚后所得共同制,其立法旨意即在于鼓勵通過夫妻合力,共同致力于婚姻家庭共同體建設,為使夫妻雙方將其所得不分彼此地用于營造婚姻家庭生活,立法將夫妻一方或雙方所得以共同財產的形式確定下來,以維護婚姻家庭這一倫理實體的穩定運行。夫妻共同債務是夫妻共同財產的消極形式,夫妻債務法是夫妻財產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認定夫妻共同債務應與夫妻共同財產制的立法旨意保持一致,即營造婚姻家庭生活,維護婚姻家庭穩定。因此,以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論作為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標準,符合我國夫妻財產制的立法精神。
第二,符合夫妻財產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在法的范疇內,權利與義務相一致是永恒的經驗法則。夫妻債務法領域理應如是。夫妻一方或雙方從所負債務中獲益,其享受了此債務帶來的權利,就相應承擔清償債務的義務。依此,若所負債務用于婚姻家庭生活,夫妻雙方從中皆獲益,則其應承擔清償債務的義務,此債務應為共同債務,這符合夫妻財產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
第三,符合國外大多數國家夫妻共同債務之一般認定規則。在國外,大多數國家夫妻共同債務立法即采“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論”標準,如法國民法典第1409條規定,為維持家庭日常開支與子女教育的費用,夫妻雙方應當負擔的生活費用以及締結的債務,屬于永久性負債(共同債務)。《德國民法典》第1438條規定,夫妻在共同財產制下,管理共同財產的配偶一方因實施法律行為所產生的債務,應經另一方同意或不經其同意但為共同財產利益計算,應認定為共同債務。《瑞士民法典》第166條規定,配偶任何一方于婚姻存續期間,代表婚姻共同生活處理家庭日常事務,配偶一方的行為在被認為是代表婚姻共同生活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責任,配偶他方應承擔連帶責任(共同債務)。因此在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設計上,應堅持以“家庭共同生活目的論”為標準,這不僅有利于我國婚姻法學者參與國際學術的交流和對話,而且亦有利于涉外婚姻的處理。
(二)“家庭共同生活”之界定與標準
夫妻共同債務之認定以所負債務實際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為標準,關鍵在于如何認定“家庭共同生活”。我國婚姻法就此并未給予明確界定,實務中法官斷案時常以日常經驗法則進行判定,是否認定為共同債務,信憑法官自由心證裁量之,生活世界冗繁多變,“家庭共同生活”認定標準之缺失易造成法官斷案不公之局面,因此為便于統一適用法律,我國立法應對“家庭共同生活”的內涵作出明確界定。 在理論界,我國學者對此認識尚存歧異。有學者認為,“通常因居屋之租賃及修繕,庭園之整理栽植,夫妻及子女衣物之購買及修補,生活物資、藥物及日常家用品之購置,報紙雜
志之訂閱,住室之裝修,仆役之雇傭,疾病之醫療,家用車輛之維持”,均屬家庭共同生活的范疇,但“因配偶一方職業或營業所成立之債務,例如補助人之雇傭,營業車輛之維持”,則應排除在為家庭共同生活所生債務之外[4]。有學者認為,因“家庭共同生活”所生債務應為純粹的生活費用,并不包括夫妻共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生債務,但二者在性質上同屬夫妻共同債務[5]。還有學者認為,夫妻在婚姻期間因實施違法行為所欠的債務應屬為“家庭共同生活”所生之共同債務[6]。
筆者認為,夫妻因締結婚姻而形成倫理意義上的家庭共同體,在婚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或雙方實施的法律行為,只要有益于婚姻家庭利益,且家庭共同體成員從中分享利益,皆應歸入為家庭共同生活而進行行為的范疇,因此,應對因“家庭共同生活”所負債務作廣義理解,具體言之,應包括三種類型:
第一,純粹性日常家庭生活開支所生債務。如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共同購置修建婚姻家庭住房所生債務;購買家庭生活用品、支付生活開銷所生債務;履行撫養教育子女、贍養老人等法定扶養義務所生債務;為具有扶養義務的家庭成員治療疾病所生債務;進行正常且必要的精神文化娛樂活動所生債務。
第二,夫妻共同生產、經營所生債務。如夫妻共同從事個體工商業、農村承包經營所生債務;夫妻合意由一方以共同財產投資經營所生債務;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籌資開辦獨資企業但收入用于共同生活所生之債務。
第三,夫妻因共同實施違法行為所生債務。此類債務是一種較為特殊的夫妻共同債務類型,其產生并不基于夫妻雙方向第三人舉債的意思表示,而是基于其共同的違法行為所造成的懲罰性或補償性后果[7]。如夫妻因共同實施侵權行為而給予第三人的損害賠償所生之債務;夫妻因共同實施犯罪行為而繳納罰金所生之債務。
基于上述對因“家庭共同生活”所負債務的正面界定,筆者認為,還應從其反面對所負債務確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形予以明確列舉排除,以使其邏輯更趨周延。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17條之規定值得借鑒,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其所列舉的情形并不能反映已深刻變化了的社會存在,如夫妻一方給第三人提供連帶責任保證形成的擔保之債,夫妻分居期間一方所借之債等問題則因法無明文,游離于法律之外。
關于婚姻期間夫妻一方給第三人提供連帶責任保證形成的擔保之債的定性問題,筆者認為,應從兩個層面考慮。第一,鑒于夫妻共同債務之認定以所負債務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為標準,此擔保之債務事實上確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夫妻另一方亦未從其中獲益,因此應認定為夫妻個人債務,由夫妻提供擔保一方以個人財產負責清償。第二,鑒于現代民法以私法自治為理念,尊崇個人意思表達之自由,若此擔保之債已經夫妻雙方合意或獲得夫妻非擔保方事后追認,則可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由夫妻共同財產負責清償。
關于夫妻分居期間一方舉債的定性問題,筆者認為,鑒于分居期間夫妻已經中止同居生活的事實,夫妻一方所負債務的性質認定應區分情況,給予公平合理的界定。若夫妻一方所負債務是用于撫養教育子女、贍養老人等履行法定扶養義務之目的,則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若夫妻一方所負債務是用于其個人不合理消費、從事賭博吸毒等非法活動的,則應認定為個人債務。這些
應由舉債方以個人財產負責清償,但夫妻非舉債方同意以共同財產清償的除外。
(三)“家庭共同生活”之舉證責任分配及承擔
“誰主張,誰舉證”是我國民事訴訟法確立的舉證規則,若當事人一方不能對所主張事實提出足以讓法官形成內心確信的充分證據,則應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筆者認為,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舉證規則上,若嚴格依照“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要求債權人舉證證明債務人所借之債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事實,實有“強人所難”之嫌。原因在于,家庭之于社會乃為相對封閉的倫理實體,其家庭成員的身份地位、財產關系及生活狀況等信息,因缺乏公示性,外界無從知曉。故在夫妻債務法領域,夫妻一方所負債務是否用于共同生活,債權人難以知情,若讓其承擔證明責任則顯失公平。事實言之,對于夫妻一方或雙方舉債,其用途是否為家庭共同生活,只有夫妻舉債一方或共同分享了所負債務帶來的利益的夫妻當事人知情,而且“因
夫妻人身關系的原因使得夫妻一方更有能力和條件掌握有關債務用途的信息,夫妻一方更容易取得相關證據。”[8]因此從實現公平正義的價值維度考量,夫妻當事人應當承擔舉證所負債務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證明責任。
具體言之,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舉證規則設計上,應區分兩種情況,制定不同的舉證規則,公平分配證明責任,以使債權債務當事人的財產利益得到平等保護。
第一,以夫妻名義共同舉債之情形:在實務中,夫妻雙方共同向第三人舉債,此類債務認定舉證較為簡便,債權人僅提供證據證明存在債權債務的事實已足,比如提供由夫妻雙方共同簽字的合同書等。因該債務是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應認定共同債務,由夫妻共同財產清償。
第二,以夫妻一方名義舉債之情形:以夫妻一方名義舉債,其債務可能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可能僅用于滿足夫妻舉債一方個人消費,此類債務因涉及夫妻舉債一方、非舉債一方及債權人的財產權益,在債務定性方面不能輕率地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因此,在舉證責任上,不能簡單地適用“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筆者認為,應以追求實質公正的價值理念為指針,設立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公平分配證明責任。具體言之,債權人僅須提供證據證明與夫妻一方存在債權債務關系事實,至于該債務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應由夫妻雙方舉證證明之。若夫妻舉債一方能夠舉證證明該債務確系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而非舉債一方不能提供相反證據的,該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若夫妻舉債一方主張該債務系用于共同生活,但卻無法提供證據證明,而非舉債一方卻能夠提供證據證明該債務系用于滿足夫妻舉債一方個人消費的,該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個人債務。 四、制度重構:完善我國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之立法設計
上文已對我國現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予以剖析和反思,并對其價值理念進行梳理和澄清。筆者認為,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的設計,應以尋求婚姻家庭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和諧統一的價值理念為指導,以舉債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為主旨,合理分配證明責任,以衡平保護夫妻雙方當事人及債權人財產利益,使法之公平正義價值得以彰顯和體現。
具體言之,在立法體例上,可以借鑒我國《婚姻法》第17、18條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規定時所采概括、列舉及排除式的做法,對夫妻共同債務亦采此體例。在條文設計上,為便于適用法律,可對夫妻共同債務的類型予以明確,同時從反面對不宜認定夫妻共同債務的情形予以規定,以使概念周延和具有邏輯性。基于此設想,筆者擬對我國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規則提出如下立法設計。
第×條 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或雙方基于維護婚姻家庭利益考慮,所負債務確用于婚姻家庭共同生活的,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由夫妻共同財產清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一)為維持日常家庭生活開支所負的債務;
(二)履行夫妻扶養義務、撫養子女、贍養老人所負的債務;
(三)夫妻雙方共同從事生產、經營,或夫妻一方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但其收益用于婚姻家庭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
(四)夫妻雙方共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所負的債務。
(五)其他應認定為夫妻雙方的共同債務。
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負債,債權人主張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但夫妻非負債一方提出異議的,由夫妻非負債一方提供證據證明該負債并未用于婚姻家庭共同生活,舉證不能或證據不充分的,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第×條 下列債務不能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應由夫妻個人財產清償:
(一)夫妻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資助與其沒有撫養義務的親朋所負的債務;
(二)夫妻一方未經對方同意,獨自籌資從事經營活動,其收入確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
(三)夫妻一方未經對方同意,擅自給第三人提供連帶責任保證所負的債務;
(四)夫妻分居期間,夫妻一方所負的債務,但該債務用于撫養子女、贍養老人等履行法定扶養義務的除外;
(五)其他應由個人財產清償的債務。
參考文獻:
[1]蒲純鈺.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j].社會科學家,2010,(12):76.
[2]劉萍.我國夫妻債務制度立法反思[j].學術論壇,2006,(6):141.
[3]唐雨虹.夫妻共同債務推定規則的缺陷與重構[j].行政與法,2008,(7):109.
[4]史尚寬.親屬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414.
[5]余延滿.親屬法原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57.
[6]陳葦.婚姻家庭繼承法學[m].北京:群眾出版社,2005:258.
[7]吳衛義,張寅.法院審理婚姻家庭案件觀點集成[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346.
[8]周姝.論夫妻共同債務確認制度的完善[j].法治研究,2009,(9):5.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les of marital common debts
jiang dawe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ules of marital common debts shall pursue the harmony between marital benefits and social interests, and take the debts’ purpose as a standard which the debts shall be used for marital life. the marital common debts rules shall definitely make distinction by the types of debts for marital life, and establish the legislative styles by applying generalization, particularization and exclusion followed the styles of the family law concerning marital common property. in lawsuit, it shall adopt the rules of inversion of onus probandi, and distribute the burden of proof equitably to equally protect the marital benefits and debtors’ interests.
第4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結臺我國l950年婚姻法和l980年婚姻法的相關規定.分析新婚姻法在夫妻產制度上的修改和進步.在此基礎上探討該法在立法價值取向上的變化及其原因.并指出該法在夫妻財產約定形式方面規定的不足.建議引入登記制度,增強約定的公示力.保證約定的有效性印確立性。
一、現行夫妻財產制度的架構設置
新婿姻法規定r夫妻共有財產制、約定財產制和個人特有財產制三種財產制,三者共同構成我國的夫妻財產制度。和l980年婿姻法柯1比,新婚姻法堅持了共有財產制.增設廠個人特有財產制,突出了約定財產制。
(一)關于夫妻共有財產制
依新婚姻法第十七條的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除雙方另有約定外,在 法律 規定的范圍內均屬于雙方共同所有的財產.雙方擁有平等的所有權。其中法律規定的共同所有財產范圍包括:婚姻關系存續期問一方或雙方的工資,獎金;生產經營所得的收入:知識產權收益及未明確規定為夫妻一方所有的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這說明新婚姻法同前兒部婚姻法一樣,首先將夫妻共有財產制列為基本的法定財產制。這是因為保護婚姻家庭和公民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權益是婿姻法州整婿姻家庭關系的基本準則.而夫妻共有財產制可以if{好的實現這一準則。具體而言,夫妻關系的本質決定r婚姻家庭的物質保障功能,而目前我國大多數公民的物質生活保障還離不升婚姻家庭,所以要堅持共有財產制.以彰現這種保障功能。同時現實中婦女的就業機會和 經濟 收入普遍少于男子,而且往往承擔著較多的家庭勞動。如果打著男女平等的旗號強州夫妻財產分別所有制就會在實質上造成刈女方的不平等因此采取共有財產制也有利于保護家庭中弱勢方的利益。
與前兒部婿姻法不同的是,新婿姻法明確限定r共有財產的范圍。l950年婿姻法采取_『夫妻一般共有財產制.將夫妻雙方的全部財產都納入共有財產的范圍;1980年婚姻法確立了婚后所得共有制,將共有財產的范圍限定在婿姻存續期間取得的財產;新婚姻法則通過列舉的方式.進一步限定了共有財產的范圍。共有財產范圍的縮小體現出婿姻家庭保障功能的有限性或者說相對性.為婿姻關系中個體的權利留出_『更大的空間。
(二)關于個人特有財產制
依新婿姻法第十八條的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和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用、遺囑或贈與合同中明確規定只fj]夫或妻一方的財產~方專用的生活用品等為一方所有的個人財產。該條增設了個人特有財產制,是新婿姻法一個突出的變化,體現了對個人財產的肯定與保護。
實際上1980年婿姻法中確定的婿后財產共有制已經體現出『l時個人財產的肯定.即承認婚前財產應為夫妻各方所有。但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婿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又規定:共有財產包括一方或雙方繼承或受贈的財產;一方婿前個人所有但婚后由雙方共同使用經營的財產.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生產資料經過8年.貴重生活資料經過4年后可視為夫妻共有財產。也就是說.本為夫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會因婿姻關系的延續而自動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這和婚后所得共有制的原則有所不同。從保護個體權利角度來看,《意見》的這些規定把本為一方所有的財產和一方因繼承、受贈取得的財產納入共同財產的范圍.模糊了夫妻各自所有財產和共有財產的界限,忽視了對個體財產權利的保護,同時也違背了被繼承人、贈與人處分自已財產的意志。因此引起民法學者的諸多批評。
今天,隨著
二、對現行夫妻財產制規定的評價
(一)立法價值取向的變化
綜合三部婚姻法來看,l950年婚姻法采取夫妻財產一般共有制,極力強洲了婚姻的保障功能l980年婚姻法采取婿后所得共有制并提出廠約定財產制,在保證婚姻保障功能的同時開始肯定個人財產權利。l993年的《意見》使這一傾向有所動搖,體現出趨勢和現實的矛盾和協調。新婚姻法則明確限制共有財產的范圍,增設個人特有財產制,完善約定財產制,鮮明地體現出對個人財產權利和塒意思自治的尊重與保護如前所述,夫妻共有財產制強凋的是刈婚姻家庭的保障功能,而個人特有財產制和約定財產制財體現對婚姻關系中個體財產權利和意思自治的肯定和尊重。因此從三部婚姻法規定的變化中我們可以明娃感受到:在婚姻法立法中婚姻家庭的保障功能在逐步淡化,而對個人財產權利的保護和對意思自治的尊重則在逐步加強。現在不再是共有財產制一統天下,而是三種財產制互豐h補充,互卡h衡平.共同調整夫妻財產。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婚姻立法的價值取向已從單純的強調婚姻保障功能轉到r塒保障功能和個體權利的并重上來,注重平衡保障功能和尊重個體的關系。同時現行婚姻法對約定時產制的進一步重視,對于滿足觀念與價值標準日益多樣化的嬌姻主體的需求,適應社會新的價值取向的變化有著尤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5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關鍵詞:夫妻財產制 法定共同財產 婚后父母出資購房 婚姻法司法解釋 離婚財產分割
2001年我國婚姻法施行后,為了更好地指導司法實踐,更好地貫徹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4日出臺了《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主要是內容包括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的處理程序以及其法律后果、子女撫養費的問題、提出中止探望權的主體資格和離婚損害賠償等問題。此后于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臺了《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主要內容包括軍人復員費、自主擇業費的處理、夫妻債務、住房公積金、知識產權收益等款項的認定、彩禮應不應該返還等問題。為了更加準確地處理近年來出現的各類家庭糾紛,及時高效的審理此類案件,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3日公布并實施了《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三)》。這次出臺的司法解釋,一經公布便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熱議的浪潮,此解釋共19個條文,內容主要包括夫妻房產、第三者、生育權等問題,重點規定了一方婚前貸款所購但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共同財產還貸的不動產的歸屬問題、父母為子女結婚所購房產的歸屬問題、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的收益歸屬問題以及結婚登記瑕疵處理問題等等。此次《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的出臺,對于落實司法為民的精髓,正確、合法、及時高效的審理婚姻家庭糾紛的案件,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將針對此次解釋三的重點條文進行分析,希望借此為婚姻家庭關系立法的發展進步有所作用。
一、婚姻法解釋(三)的重點內容
1、第五條規定: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七條明確規定: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生產、經營收益以及知識產權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有平等的處理權。而《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明確規定一方以個人財產投資所得的收益為夫妻共同財產,但是對孳息以及自然增值是否應歸于夫妻共同所有未作出規定。而在《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中,明確指出孳息和自然增值不是夫妻共同財產,這也是我國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進步。
2、第七條規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
由雙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該不動產可認定為雙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資份額按份共有,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婚后父母為子女所購房屋的歸屬問題自解釋三頒布以來一直是人們爭論的重點,這也是此次司法解釋變更最大的一條,解釋二規定了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夫妻雙方所購置的房屋出資的,此出資應該視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從解釋二的這一點可以看出,一般情況下,父母為子女婚后所購房屋均視為夫妻共同財產。對于《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所做出的巨大改變,我認為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著眼于我國婚姻家庭現狀,將產權登記的主體與明確表示其贈與自己子女的一方關聯起來,使父母出資購房的真實意圖得到具體體現。也比較公平地權衡了父母與夫妻雙方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很多隱患,不利于保護經濟能力較弱一方的利益,不利于維護夫妻雙方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
3、第十條規定:夫妻一方婚前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個人財產支付首付款并在銀行貸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不動產登記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離婚時該不動產由雙方協議處理。
依前款規定不能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該不動產歸產權登記一方,尚未歸還的貸款為產權登記一方的個人債務。雙方婚后共同還貸支付的款項及其相對應財產增值部分,離婚時應根據婚姻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原則,由產權登記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補償。
這一條無疑引發了人們的熱議,關于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購買婚后共同還貸的房產歸屬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房產在婚姻家庭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在以往的大部分中國家庭中,購房一般是男方家庭負擔,女方一般負責家裝,但是在房價日益飆漲的今天,房產升值,男女家庭的不對等也日益凸現出來。從另一方面來講,現今社會,沒有房產不結婚的思想越來越融入社會,大多數女性希望通過結婚來給自己掙一套房產,為以后買個保障,但是,《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的出臺,很大程度上沖擊了她們的利益,則有可能影響到婚姻的穩定。但是,我認為,此條例的出臺對于婚姻的持續發展是有著積極地作用的,對于在婚姻關系中強調男女平等、凈化婚姻締結基礎等有著重要的作用。
二、婚姻法解釋三所帶來的改變
我國實行婚后所得共同制,雙方在沒有約定的情形下,而且婚后所得財產不屬于婚前財產的轉化、自然增值和孳息、法律規定專屬于一方的特定財產或者遺囑與贈與一方排除共有的情形的,都應當由雙方共同共有。在沒有約定和法定范圍之外的財產根據婚姻法只能定為夫妻共同財產,這一規定顯然無法解決司法實務中的婚姻財產糾紛疑難問題,因此婚姻法解釋(三)的出臺就是側重解決司法實務,重點就夫妻財產歸屬認定和分割方面。這里著重理解司法解釋(三)第七條的適用和爭議。第七條和第十條這兩條都屬于《婚姻法》第18條的婚后一方個人財產范圍,體現了解釋(三)更注重于根據財產來源而非根據財產取得的時間確定歸屬的價值取向,也就是更注重保護婚姻關系中的個人財產權利。這個立法背后的價值體現顯然與婚姻法共有基礎的立法思想相悖,因此出臺至今,很多人仍然認為新的婚姻法解釋更多的是在保護私權,而非基于婚姻家庭的團結共有,很多普通百姓更多的認為該解釋是在保護婚姻關系中占主導經濟利益一方的利益。
在中國,房產對于很多婚姻和家庭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房價高居不下的中國,很多剛結婚的年輕夫婦無力購買房產,父母出資購房的現象很普遍,也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父母出資為子女購房的認定是司法實務中必須明確的內容,而且應當盡可能的符合婚姻法立法的愿意。可是此次《婚姻法》通過司法解釋(三)來彌補司法實務的難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在父母出資購房的認定方面并沒有統一的標準,沒有起到司法解釋本應發揮的作用。從首例婚內房產加名案引起的各界爭論來看,并沒有達到明確判案標準、減少同案不同判的作用。首先,《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七條沒有具體說明父母出資買房是出全資或者是出資首付款的情形。如果只認定為贈與單方,對于婚后房產名下另一方一直按共同財產還貸的情形有失公平。法院對解釋(三)的理解并沒有遵循《婚姻法》夫妻共有的前提,解釋(三)的立法也完全了《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的相關規定。這讓很多現實中的婚姻家庭關系因為房產而變得異常的敏感。
綜上所述,既然《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七條對于父母出資為子女購房第一款中并未明確規定父母出資是全額出資或者部分出資,我認為應該推定該解釋是指父母出資全額為子女購房并登記在子女名下的情形。這樣的推定遵循的是《婚姻法》夫妻財產共有的原則,也是保護經濟相對弱勢方,維護婚姻雙方在婚姻生活中平等的地位,更好的維護婚姻家庭的和睦團結,更有利于維系婚姻雙方的關系,能給對方更多的安全感。畢竟沒有人是奔著離婚去結婚的,也沒有人想在未結婚時候就因為房產和心愛的人撕破臉皮,這也不符合中國這個人情社會的處事方式。如果因為房產而失去愛情、失去婚姻的和諧、失去信任和安全感,那這法律的解釋就沒有起到保護婚姻的作用,別讓愛情婚姻過不了房子這一關。《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實施半年多以來,許多類似案件的審理判決并沒有因為解釋的頒布實施變得明確,不論從立法原意還是立法價值上都無法體現立法者鮮明的態度。站在《婚姻法》的立法應忠實原則的立場,討論司法解釋原應有的作用,司法解釋必須講邏輯,那是司法的生命。邏輯不能苛責偏好,但偏好更不能改變邏輯。家庭倫理道德與私有權的保護在婚姻法中原本就是相互碰撞沖突的,如何權衡兩者靠的是立法,正確的立法本意能是司法實踐的根本依據,也是判案的關鍵所在。顯然《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在權衡這一問題的時候沒有達到應有的目的,立法在權衡道德與私有權的保護中全身而退,卻引得一片爭議。盡管如此,此次解釋的頒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婚姻家庭領域立法的一大進步。在保護夫妻共有財產的法律道路上又向前行進了一大步!
本項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型科研項目資助,文章編號:CX2011SP38
參考文獻:
第6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關鍵詞】夫妻財產制;物權法;調試
我國的《婚姻法》是關于處理夫妻間財產關系的法律硬性規定,而《物權法》是婚姻家庭成員之間財產關系處理的基礎性法律,為公民處理婚姻家庭中財產糾紛提供了更加具體的針對公民個人私有財產的法律保障。本文則研究的是某些夫妻財產制度與《物權法》的沖突問題研究。
一、夫妻財產制度與《物權法》存在沖突
父母贈與婚房的法律沖突。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該不動產認定為夫妻一方個人財產。根據《物權法》規定,出資方父母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權,即所有權仍屬于房地產商,此行為屬無權處分行為,房屋贈與合同效力待定。出資方父母作為買受人,所登記的權利人與買賣合同的買受人不一致,更無法將房屋產權登記在出資方父母子女名下。
投資收益的爭議。資本收益系因投資者通過低買高賣等技術層面的操作所產生的投資證券的交換價值的增加,并非基于原本為他人用益所產生的對價收益,因此不屬于法定孳息范疇與自然增值,不適用于《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就《婚姻法司法解釋(二)》規定,一方以個人財產投資取得的收益,屬于共同財產。而《物權法》規定,私人對他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動產和不動產享有所有權,以及私人合法的儲蓄投資收益都受法律保護。
約定夫妻財產制與物權法的沖突。我國常出現夫妻間契約效力認定問題以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除“重大理由”外,不得分割共同財產的問題。但從物權法角度講,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無明確約定的,可以隨時分割一部分買賣或將其物權轉讓。
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爭議。在物權法所規定的保護措施里, 包括返還確認, 確認權力, 返還原物, 排除防礙, 消除危險要求修理重做, 恢復原狀, 賠償損失這樣的內容。而婚姻法對返還請求權卻不明確,尤其對于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除“重大理由”外無特別規定的返還請求權更是與物權法規定相沖突。
二、我國夫妻財產制度與《物權法》存在沖突的原因
婚姻法自身規定不足。現行的婚姻法主要規定夫妻財產的所有權,對于財產的使用、管理、變更、終止,均未分別作出明確規定。約定夫妻財產關系何時生效、變更以及如何變更等問題;約定財產制對內效力所有權認定方面也是現行婚姻法所要解決的問題。
物權法自身規定的缺陷。不動產登記機關責任、權利不明確,我國登記制度雖然采取實質審查主義、登記生效主義;對于由于登記機關的錯誤而造成權利人損失的,法律之規定登記機關有變更義務,而真正權利人的損失卻無法得到有效的救濟。登記薄記錄不完整,使得查詢很困難。我國一律規定非登記不發生物權變動的效力,就是物權法規定與其它部門法產生沖突。
立法目的的差異。婚姻法主要是調整婚姻家庭關系,包括人身財產關系。而婚姻法要立足與保證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物權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因物的歸屬和利用產生的財產關系,其立法目的則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明確物的歸屬,發揮物的效用,保護權利人的物權。
三、調適我國夫妻財產制度與《物權法》的建議
(一)完善我國現行夫妻財產制度
應明確夫妻財產約定時間及生效時間。夫妻婚前訂立財產契約的,于雙方結婚之日進行登記時起生效;婚后訂立財產契約的,于雙方訂約且在婚姻登記機關登記之日起生效。建議明確規定夫妻財產約定與婚前登記無效情形及其法律后果。無效或效力待定的夫妻財產約定與父母贈與婚房登記瑕疵自始無法律約束力,對夫妻雙方及第三人均不產生法律效力。
明確《婚姻法》中的“投資收益”。一種情況是,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非應對方“協力”幫助下而產生的市場價值的增加。即該財產婚后市場價值的增加既可能是財產所有人自己完全付出努力的結果。其最大特點是收益的產生并沒有收到對方“協力”幫助。另一種情況是,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因另一方在婚后“協力”而導致的市場價值增加。非因對方“協力”產生的投資收益,屬于個人財產。
(二)夫妻財產處理無相應法律救濟引用物權法
明確夫妻財產對外公示方式。筆者建議立法更多的增加夫妻財產公示問題。確立夫妻財產約定契約變更或撤銷的具體程序;建立夫妻財產登記認定審查程序,以書面形式作成的約定,原約定書是經過公證的,變更、撤銷協議還須經過公證程序。如果夫妻對財產契約的變更或撤銷無法達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夫妻可通過法院訴訟程序解決變更或撤銷約定的法律后果。
我國《物權法》第九十九條規定,共有人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動產或不動產,按份共有人可以隨時請求分割。因分割對其他共有人造成損害的,應當給予賠償。”無疑,將《物權法》的這一規定引入夫妻財產制度,以此解決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或者婚內侵權等情形的夫妻財產分割問題,能使夫妻財產制度更完善,隨之也調和了夫妻財產制度與《物權法》的沖突。
參考文獻
第7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25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下稱《解釋三》),并自2011年8月13日起開始實施。該司法解釋共19條,涉及親子鑒定、婚內財產分割、妻子單方面中止妊娠等多個方面的內容,其中,有關房產問題的兩條規定所引起的關注與爭議最多。《解釋三》第7條規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由雙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該不動產可認定為雙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資份額按份共有,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第10條規定:“夫妻一方婚前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個人財產支付首付款并在銀行貸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不動產登記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離婚時該不動產由雙方協議處理。依前款規定不能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該不動產歸產權登記一方,尚未歸還的貸款為產權登記一方的個人債務。雙方婚后共同還貸支付的款項及其相對應財產增值部分,離婚時應根據《婚姻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原則,由產權登記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補償。”
媒體和學界對《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之規定的批評不絕于耳,究其緣由,擔憂這兩條規定弱化了法律對家庭中的弱者(主要為女方)的保護,進而將擴大男女兩性之間在實質上的不平等,可謂是其成為眾矢之的主要原因。有論者認為,這種“公婆買房、兒媳沒份”的現象違反我國傳統的婚姻倫理,破壞了“修齊治平”的家國文化,它勢必將嚴重沖擊甚至于摧毀為國人奉行千年之久的婚姻倫理價值。摒棄特殊的國情和傳統文化對婚姻家庭關系的影響,違反“筑巢引鳳”的生物定律和性別分工的社會定律,一味地推行“誰投資誰受益”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司法的社會認可程度將會大打折扣,司法的實際功效將無從產生,司法的權威將逐漸損減殆盡”。 還有學者甚至稱其為“吹響了‘中國家庭資本主義化的號角’”,認為這樣的規定是“以個人主義壓倒家庭價值,使得涵養道德、培養善良風俗和民情的家庭細胞,感染上個人理性算計的病毒,父慈子孝傳統將煙消云散”。若將這一資本主義的個人財產原則引入中國的婚姻實踐,“破壞的就不僅是婚姻,還有人心”。
然而,這些口誅筆伐也引發了人們的思考:《解釋三》的改弦更張是否意味著我國的婚姻家庭法對女性和婚姻的立法理念發生了轉向?是否真如學者所說,是一個“調撥婚姻家庭關系、敗壞人倫親情”的“離間者”?
二、離婚房產規定的法律述評
《解釋三》的進步意義不言而喻。無論是從理論體系的厘清還是在司法實務的操作上,離婚房產規定的立法設計都是進步得,其積極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符合《婚姻法》夫妻財產制的發展趨勢
建國以來的《婚姻法》在夫妻財產制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從“夫妻一體主義”向“夫妻別體主義”轉變的趨勢。“一體主義”的財產立法傾向于將婚前和婚后的財產盡量納入夫妻共有財產。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規定:“雖屬婚前個人財產,但已結婚多年,由雙方長期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均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6條規定:“一方婚前個人所有的財產,婚后由雙方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生產資料經過8年,貴重的生活資料經過4年,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而“別體主義”的財產立法則會盡可能增加夫妻個人財產的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一改先前的慣例,明確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不會因為婚姻的延續而轉化為共有財產。《解釋三》更是將婚后取得的贈與房屋和獲得產權的按揭房屋從共同財產的范圍中劃分出來。可見,我國的法律制度對女性的保護卻是越來越全面的,并沒有隨著財產制的變化而減弱。《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恰符合現代家庭立法從“一體主義”向“別體主義”的發展軌跡,更側重于對女性的財產獨立與人格獨立予以雙重保障,不僅回應了新時代的性別平等訴求,也實現了立法理念的更新。
(二)符合《物權法》與《合同法》的基礎原理
依據“物權性的期待”理論,在物權合意做出后,獲得產權前,買受人享有物權期待,此時的債權具有物權的屬性。 買受人財產形式從債權到物權的變化都僅圍繞其自身為主體而發生,在買受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到獲得房屋產權證期間,插入一個結婚法律行為也不能改變按揭房屋為婚前個人財產的權屬界定。在“物權公示原則”下,按揭房產的取得與變更皆以權屬登記為依據,締結婚姻關系不能產生所有權變動的法律效力。
從合同的“相對性”理論出發,僅在買受人和銀行之間存在的債權債務關系既無需公示,也沒有因婚姻關系的變化而當然地將所欠貸款從個人債務轉化成為夫妻共同債務。“婚后以夫妻共同財產還貸,相當于買受人的配偶以默示的方式自愿償還他人債務,是典型的債務承擔行為”。 它只能在雙方之間產生債權返還請求權,而不是共有關系。值得注意的是,《解釋三》明確規定按揭房屋的首付方必須對另一方婚后還貸的款項及其相應的財產增值給予補償,此處實為新司法解釋的閃光點。
(三)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則
父母出資為子女購房所形成的是民法上的贈與法律關系。在此問題上,原權利人(出資父母)的意思表示對于財產的移轉起決定性的作用。從尊重現實的角度出發,由法律明確規定獲贈房產僅登記在出資父母的子女名下,即視為父母做出僅將房屋贈與自己子女而不包括其配偶的意思表示,也是最具有可信性、最接近贈與人真實意思和最符合民法意思自治之基本原則的法律推定。將獲贈房屋一概認定為夫妻共有財產很可能導致出資父母用大半生積蓄為子女買房但其子女在離婚時卻沒分得房子的不幸結果,這將嚴重違背贈與人的意愿和利益,完全違背民法的意思自治
原則。如此一來,夫妻雙方的“財產自治”就被架空,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則也將嚴重減損。《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正是從民事法律關系的角度出發所做出的修正,明確承認了父母贈送房產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對自己兒女做出的這一“利己”的事實,使得贈與合同的標的不會因為離婚析產而“改名易主”。 三、離婚房產規定的助推效能
將《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放到更加寬闊的視野中,它將對現存法律體系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對此,我們不妨大膽的預測一下。筆者認為,它的助推效能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訴訟模式的轉變和契約精神的弘揚
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同仁反映,簽訂婚前協議的情況悄然增多,極具可能性的一個后果便是,以后離婚訴訟的模式或將有所改變——不僅僅是在法庭上進行博弈,還有簽訂婚前協議時的較量,其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中最直接的便是司法成本的節約和訴訟效率的提升。加之,雙方當事人于擇偶時、結婚時就已經明確了各自的權利義務,那隨后一系列的行為也將不再盲目,整個社會活動的成本也將隨之降低。另外,在個人財產權利優先原則確立后,當事人對雙方財產關系的自我治理將得到增進,進而,社會整體的契約精神也將得到推進。這種重視契約精神的私法理念既是發展市場經濟的結果,也會反過來促進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它對市民社會的形成、私法體系的完善和法治國家的建設都至關重要。
(二)傾向性立法的重視
有學者一言蔽之的指出,對離婚房產問題的爭議“實質上可以歸結為到底要用夫妻財產共有制還是用夫妻財產分別制來實現男女平等的問題”。 德國、英國、瑞士以及中國臺灣等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所采取的夫妻財產分別制在實際操作上的方法對保護女性、實現兩性平等這一立法目標有著異曲同工、殊途同歸的效果。在分別財產制下,女性擁有獨立的財產權和人格權,其實際上的劣勢可以通過規定家庭共同生活費用主要由男方承擔、增加離婚扶養費的數額、或者男方對女方做出補償等等制度來彌補。 畢竟,法律對權利的保護遵循的是其特有的發展規律,即“無財產即無人格”。
(三)婚姻家庭法多元化發展進程的開啟
較之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有關父母婚后贈房的法律規定,離婚房產的權屬界定使得女性從婚姻中得到的利益卻不如前,其婚姻投資的熱情也有所降減。在女性經濟地位普遍提升、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健全、職業發展限制減少、教育年限不斷延長等諸多復雜的社會背景之下,國人的婚戀行為表現出初婚年齡推遲、離婚率攀升、非婚同居悄然增多等現象。婚姻對女性的吸引力降低了,非傳統家庭的不斷涌現給婚姻家庭法的適用情形提出了新的挑戰。新司法解釋的規定使得回歸家庭與發展事業的選擇會導致女性在離婚時將面臨截然不同的財產境遇。家庭形態的推陳出新必將促使“婚姻”一統天下時代的結束,而家庭法多元化發展的進程也將隨之開啟。
第8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關鍵詞:婚姻法;夫妻財產制度;立法缺陷;立法建議
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的實施已成為千家萬戶關注的熱點,其中財產制的設立又是人們關注的熱點之一。婚姻財產制度,也稱夫妻財產制度,是指規范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財產的歸屬、使用、收益、管理及婚姻關系解除時財產清算等問題的法律制度,其核心內容是夫妻財產所有權的歸屬問題。《婚姻法》對于夫妻財產制度的立法選擇是將目前我國夫妻財產制度實行的法定財產制和約定財產制相結合,夫妻雙方對財產有約定的,適用約定;沒有約定的,婚后共同所得為法定財產。這種修改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婚姻法》對于夫妻財產制度規定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本文試通過對現行夫妻財產制度的分析,提出一些修改和完善的建議,希望能對完善我國夫妻財產制度有所幫助。
一、我國新《婚姻法》對夫妻財產所有制的修改和發展
我國1980年《婚姻法》中規定的“以夫妻財產共同制為主,以夫妻財產約定制為補充”的夫妻財產所有制形式是與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家庭生活狀況和當時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的。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人們的婚姻家庭觀念和婚姻家庭關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夫妻財產制度已不足以調適新情況下的夫妻財產關系。2001年4月28日通過的《婚姻法》修正案,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的夫妻財產制度。
(一)明確界定了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完善了夫妻共同財產制度。修改前的《婚姻法》第13條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雙方另在約定的除外。”這一規定表明,該法在夫妻共同財產上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規定的弊端是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具體范圍不明確,夫妻共同財產與夫妻個人財產的界限也不明確。修改后的《婚姻法》第17條明確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下列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1)工資、獎金;(2)生產、經營的收益;(3)知識產權的收益;(4)繼承或贈與所得的財產,但本法第l8條第3項規定的除外;(5)其他應當歸共同所有的財產。”這一規定是婚姻家庭立法方面的巨大進步。它明確了夫妻共同財產是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列舉式和概括性具體規定了夫妻共同財產的內容;明確了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續期間因繼承或贈與而獲得的收益的歸屬原則,并且,明確了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知識產權屬于夫妻共同財產的條件。
(二)明確界定了夫妻專有財產制度
夫妻專有財產制度,也叫夫妻特有財產制度,是指專屬于夫妻一方單獨所有財產的法律制度。凡屬于夫妻一方個人所有的財產,一般來說應由其本人管理支配和處理,在離婚時即歸其個人所有,不再分割;在財產所有人死亡時即作為個人遺產,按我國繼承法的有關規定處理。圈修改后的《婚姻法》第18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為夫妻一方的財產:(1)一方的婚前財產;(2)一方因身體受到傷害獲得的醫療費、殘疾人生活補助費等費用;(3)遺囑或贈與合同中確定只歸夫或妻一方的財產;(4)一方專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應當歸一方的財產。”并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9條明確規定:“婚姻法第18條規定為夫妻一方所有的財產,不因婚姻關系的延續而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從該規定可以看出,新的婚姻法不再承認夫或妻一方的財產因一定時間的經過而自動轉化為夫妻共同財產的規定。體現了民法學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則,以有效地防止和減少實際生活中有些人利用婚姻謀取不正當利益。
(三)完善了夫妻約定財產制度
所謂約定夫妻財產制,根據《婚姻法》第19條第3款的規定,是指婚姻當事人通過協議方式,對他們的婚前、婚后財產的歸屬、占有、使用、管理、收益和處分等權利加以約定的一種法律制度。《婚姻法》第19條明確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約定應當采取書面形式。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17條、第18條的規定。”本規定明確了約定的性質、約定的范圍和財產的歸屬以及約定的優先效力;明確規定在約定的方式上必須用“書面形式”;明確規定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可以約定債務的歸屬,但該約定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由此可見,新《婚姻法》適應了我國家庭財產狀況日益復雜多樣化的趨勢,使婚姻當事人在處理夫妻財產時有更大的靈活性;充分體現尊重夫妻財產問題的自主權利,維護夫妻特別是再婚和分居兩地的夫妻各方的財產利益;滿足涉外婚姻家庭的特殊需要,維護涉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以利于與國際接軌。
二、我國現行夫妻財產制的立法缺陷
新《婚姻法》中有關夫妻財產制的規定,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婚姻關系的要求,也是我國婚姻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的結果。不過,從法理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新《婚姻法》中有關夫妻財產制度的規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具體表現為:
(一)夫妻財產制總體結構不完整
從夫妻財產制的結構看,我國夫妻財產制的總體結構不完整。只確立了常態下的夫妻財產制,即普通夫妻財產制,沒有相應建立非常態下的特別夫妻財產制。應當針對夫妻分居,夫妻一方失蹤,夫妻一方虐待、遺棄另一方等特殊情形,賦予當事人請求改共同財產制為分別財產制的權利,使分別財產制作為非常財產制。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障財產安全和交易安全的要求。
(二)夫妻共同財產制存在的缺陷
總體而言,新《婚姻法》關于夫妻共同財產范圍的規定符合我國的國情,有利于保護弱者一方(特別是沒有勞動能力或勞動收入的一方)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維持夫妻關系和家庭關系的穩定。[4]但是,通過具體分析,不難發現新《婚姻法》的有關規定或者體現了事實上的不平等,或者與相關法律規定存在一定的矛盾。
1.關于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
知識產權是人身權與財產權的結合,因此。一般認為知識產權中的人身權內容只能屬于創造者自己(如作者、發明創造者),只有其中的財產權內容可以轉移(繼承、轉讓、贈與等)。正是基于知識產權的一般特性,《婚姻法》第17條規定,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知識產權的收益”歸夫妻共同所有。但是,該規定的不足之處是只強調了“知識產權的收益”所得時間,卻忽略了“知識產權”的取得時間。于是,就有可能出現兩種不公平的現象:一是一方婚前取得的知識產權,婚后獲得收益則歸夫妻共同所有;二是一方婚后創作或者創造并取得的知識產權,離婚后獲得收益卻又只歸一方所有。顯然,在前一種情況下,對取得知識產權的一方不利;在后一種情況下,則對取得知識產權的配偶對方不公。
第9篇:婚姻家庭合同范文
(一)弱者在國際私法中之界定
有人認為,在國際私法領域弱者是指在涉外民商事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或者不利地位的當事人。還有人認為弱者是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處在相對劣勢的一方。屈廣清教授認為國際私法中的弱者是指在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中需要法律給予特別保護的處于不利地位的一方。由此可見,弱者是一個相對的、有流動性的概念。
(二)弱者的法律特征
盡管難以對弱者進行明確的界定,他們在法律特征上仍存在一些共性。有學者將弱者身份的法律特征總結為以下五點身份的多重性、法定性、可變性、獨立性、社會性:也有觀點稱弱者有如下七個法律特征多重性、法定性、可變性、獨立性、社會性、相對性、不易識別性。本文認為,國際私法上的弱者具有四種明顯的法律特征。
第一,弱者身份的相對性。由于個體所處的弱者地位是在一個范圍中界定的,比如不能說婦女就是弱者,而是在婚姻家庭領域,婦女相對于男子來說是弱者。若是在消費領域中,如果婦女并非消費者,那她就不是弱者,若是在消費合同領域中,婦女處于弱者地位,那并非因為她的性別,而是此時她處于相對于生產者而言的消費者地位。
第二,弱者身份具有變動性,如婚姻家庭領域中的父母子女關系。未成年子女作為被扶養人一般處于弱者地位,而隨著時間的變化,年邁無生活能力的父母又處于弱者地位。
第三,弱者身份具有獨立性,雖然弱者的弱主要是因為市場力量、生理、信息方面與強者相比總會處于劣勢。但是在法律地位上弱者是獨立的概念,并不依附于強者,還可以獨立自主地決定是否同強者確定法律關系。
第四,弱者具有不確定性。由于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傳統大不相同,各國對國際私法領域內弱者的認識也不完全一致。例如被扶養人與撫養人誰是弱者本身就難以界定,這種不確定性亦加大了對國際私法保護弱者研究的難度。
(三)弱者的類型
由于弱者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概念,從理論上來講國際私法的任何一個領域可能都有弱者的存在,但是在實踐中,國際私法中的弱者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一,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婦女、子女、被收養人、被監護人、被扶養人;二,合同關系里的特定當事方,例如雇傭合同中的雇員、消費合同中的消費者、保險合同中的投保人等;三,侵權關系中的受害人,比如產品責任項下的被侵權人。
二、弱者保護的意義
作為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尤其是法律中的正義價值自占以來就被人們所關注。羅爾斯在分析正義之含義時將自由和平等這兩種價值結合起來,他提出了兩個基本原則。第一,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一個人都有利,并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沉。且第一個原則優于第二個原則。在他看來,實質正義是目的,而形式正義則只是作為實現該實質正義這一目的的一種方式。法律的正義體現在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這兩大方面,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實質正義顯得愈發重要。在國際私法領域也同樣如此。
法則區別說標志著國際私法理論的誕生。按照薩維尼的理論,國際私法的首要任務是根據法律關系的性質來尋找法律關系的地域上的本座,是通過指出沖突規則來對適用法作出決定:或者說,在薩維尼的眼中,國際私法只是法律適用中的立法,所適用法律的實質內容不必考慮,這樣做才能實現判決結果的一致。懷疑論者認為,薩維尼的這種方法其實并未關注實質正義。不可否認,法律應有確定性,判決結果的一致性也是不應放棄的,但同時如何使法律適用真正實現公平正義是今天的國際私法立法必須考慮的問題。換言之,沖突法再也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中立機械體系,為保持其法律確定性,沖突正義和判決結果一致性等特性的同時,也應該對法律的靈活性、實體法上正義和相關利益做一考慮汗。
以美國為例,在美國沖突法革命的前夜,最高法院對經典法律選擇理論的態度改弦易轍,其轉折性判例就是一系列適用州勞工賠償法初臨跨州事故的案件。在阿拉斯加包裝工人協會訴勞工委員會案與太平洋雇主保險公司訴勞工委員會案中,最高法院為加大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不在固守先例,而是判決雇傭所在地州與損害發生地所在州均可提供法律救濟,因為此兩州對執行本州的勞工賠償法所體現的政策均有充分利益。另外,這兩個案子表明,在跨州案件中,其他連結因素亦可能為適用本地制訂法提供合法依據。這些判例標志著最高法院對憲法與沖突法關系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在美國勞動力流動性日益增強的背景下,以上判例的實際效用在于加大了對勞動者的保護力度。通過允許數州的勞工委員會行使平行管轄權,最高法院保證了跨州雇員可以方便地選擇糾紛解決地點。如果與工作有關的事故與不止一個州有聯系,受傷雇員就有權選擇在會做出對其最有利的裁決的州主張權利。也就是說,最高法院鼓勵挑選裁決地點。盡管傳統主義者認為這一做法實不可取,但它在實際上取得了良好效果。除了影響司法實踐外,最高法院的判決還在理論界產生了重大反響,它們證明了勞工賠償這一重要領域可以不需要法律選擇規則,從而大大促進了美國沖突法的重新定位。
由此可見,為了正義的利益而背棄或放寬既定規范的要求被認為是必要的。國際私法關系具有復雜性,這就決定了我們在研究時,絕不能將一切國際私法整體視為相同人,針對客觀事實應正視差異者的存在。關注特殊個體,強調實質正義,改變傳統的國際私法調整方法,從而對不公平正義的情況予以矯正,是十分必要的。
綜上所述,國際私法作為特殊的法律部門,有其特有的制度和方法。在維護弱者利益方面,具有其他法律部分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需要以國際私法對弱者的利益進行特殊保護,有其應然性從應有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再從法定權利轉化為實有權利,是人權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實現的基本形式。從應然到法定再到實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保護弱者利益。
三、國際私法中對弱者利益之保護方法
(一)直接方法
國際私法中對弱者利益的保護方法可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直接保護方法是通過制定同意的實體化來實現對弱者利益的直接保護,包括國際公約、雙邊條約和國內立法。如1951年《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1954年《關于無國籍人地位的公約》等等。這兩個公約對難民和無國籍人的法律保護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據此難民和無國籍人的具體權利主要有:不受歧視、國民待遇、繼續居住、個人身份、知識產權、財產、訴訟、工資、經營、福利、教育、社會保障、行動自由等。由此可見,以國際公約的方式直接規定弱者的權利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十分有限。對弱者進行直接保護主要存在于國內立法中。
從立法的角度來春直接適用的法包含了對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考慮,弱者保護應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直接保護方法也有其弊端。因為統一實體規范并不能完全取代沖突規范的作用,其適用領域非常有限。如在涉外婚姻和繼承等領域,由于其帶有強烈的人身性質,每個國家的規定都不甚相同。因為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相去甚遠,所以在這些領域,依然未能制定出統一的實體法。因此,在這些領域,仍然需要由沖突法規范進行調整。
(二)間接保護方法
1.保護性沖突規范
屈廣清教授將保護性沖突規范界定為意在保護特定一方當事人的法律適用規范。保護性沖突規范并非單獨的一種沖突規范類型,而是這種沖突規范從實質取向看有保護特定一方當事人的意味。這種界定主要是為了與后文中有利于弱者的法作為系數公式的情況區分開來。本文認為保護性沖突規范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為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二為將選擇法律的權利交給特定當事方。
首先,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是對弱者利益進行保護的重要手段。如《羅馬條約》第5條和第6條規定賦予當事人意思自治選擇法律的自由,但對意思自治加以限制。比如在保護消費者利益方面《奧地利國際私法》(1978年)第41條第2款的規定,也主要以對意思自治進行限制的角度來進保護其利益。類似的做法還見于《德意志聯邦國際私法》(1986)、《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20條等等。此類做法都對當事人選擇法律作出了限制。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有利于實現對弱者的最低限度的保護。即使其所適用的法律不能充分保護弱者利益,但也是保護弱者的重要途徑之一。
其二是將選擇法律的權利交給特定當事方。這一做法主要體現在涉外侵權領域。舉例來說《瑞士聯邦國際私法》第138條、139條就采取了這一方法。這兩條就規定了侵權訴訟中的受害一方即原告有權選擇法律。此種規定的確賦予了原告方法律選擇權,但與此同時,亦增加了原告方查明法律的負擔。
2.有利于弱者的法作為系數公式
系數公式是國際私法針對各種不同性質的法律沖突對應性地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的總結,是特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和特定的法律關系一一對應的寫照。保護弱者利益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就是適用有利于弱者利益的法,即將有利于原則列入系數公式。
如1978年的《奧地利聯邦國際私法法規》第22條規定結婚生子女因事后婚姻而準正的要件依父母的屬人法:父母的屬人法不同時,依其中更有利于準正的法律。類似的例子還見于《突尼斯國際私法典》(1988年)第50條。這些條文都是要求適用最有利于弱者利益的法律。
有利于弱者的法作為系數公式優點有二:一,它有助于實現實質正義。它可以避免自眼的法律選擇規范,以有利于原則為指引,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弱者利益:二,如果將有利于弱者利益的法作為系數公式,那么在審理案件時,法官可以直接在相關法律中選擇適用能夠達到保護弱者目的的法律,從而能夠達到判決一致的結果,這也是國際私法一直所致力于追求的。
四、我國立法現狀及評價
(一)我國立法現狀
我國對弱者利益的保護也可分為實體法和沖突法兩個方面。首先,中國在憲法、刑法等等重要的實體法律中,己經體現出了對婦女、兒童、消費者等利益的保護。例如憲法明確規定了保護弱者權益,在民商法方面,也有很多條款、單行法等明顯傾向于對弱者進行保護。比如《老年人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格式條款對接受方利益的保護,婚姻家庭關系中對子女利益的保護等。
在沖突法領域《法律適用法》的頒布是一個分水嶺,將對弱者權利的保護上升到了一個新階段《法律適用法》從總則到三大分則,即涉外婚姻家庭方面、涉外合同和涉外侵權方面都體現了對弱者利益的保護。首先是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適用法》在婚姻家庭一章中,對如下三種情況進行了規定。其一是父母子女人身、財產關系,見于第25條,體現了有利原則的典型適用:其二是在涉外撫養關系中確立對被撫養人權益的保護,見于第29條:其三是在涉外監護關系中對被監護人權益進行保護,見于第30條。第二大方面是在涉外合同領域對弱者權益進行保護。《法律適用法》對涉外消費合同和涉外勞務合同都進行了另行具體規定。分別適用消費者經常居所地法律、商品、服務提供地法律、勞動者工作地法律、用人單位主營業地法律、勞務派出地法律等。第三大方面涉外侵權,見于第45條,對于產品責任規定了具體的適用規則,是將選擇法律的權利交給特定當事方的典型體現。
(二)對我國立法現狀的評價
《法律適用法》在三大領域都體現了保護弱者權益,具有十分進步的意義。但與此同時《法律適用法》對弱者的保護依然有很多不足。
首先是對弱者的概念和范圍沒有清晰的界定。由于弱者的身份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各個國家對弱者的界定以及識別方法的不同,使國際私法并無法實現保護真正意義上的弱者。因此,國際私法應該首先清晰地界定弱者的概念和判斷標準:在弱者的范圍方面,涉獵范圍越來越廣是國際私法發展的趨勢。把弱者保護僅僅局限在傳統領域顯然是不合理的。在實踐中,涉外保險投保人和交通事故受害人等等也都是背負著羸弱徘徊在法律的邊緣,把它們納入國際私法的范圍,尤其是《法律適用法》的保護范疇是十分必要的⑩。
其次是在國際私法領域保護弱者還沒有成為基本原則。實際上在各國立法中,把保護弱者當作基本原則是極少見的。但將其確立為基本原則,首先就可以彌補立法方面的不足之處,更有利于司法人員在處理案件時靈活司法,有利于真正實現實質正義。
第三是尚未引入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前文依然闡釋了對意思自治原則的限制作為保護性沖突規范的優勢。目前我國國際司法領域對涉外合同的相關規定都沒有適用此種立法模式,而其他國家己經開始采納了這種立法方式,并開始運用到涉外勞務關系、涉外消費關系等等弱者的弱勢地位體現得較為明顯的領域中。我國也應當順應潮流,引入這種立法模式,這將有助于實現對弱者利益的最低限度的保護。
第四是很多規定仍然是自眼的沖突規范。即規范本身雖彰顯了了保護弱者利益的精神,但是根據該沖突規則所指向的實體法律的規定可能會背離于保護弱者的初始目的,從而無法真正地實現對弱者的保護。比如《法律適用法》第43條、第45條對勞動合同和侵害人格權的情況的規定,從表面上看來的確是為了保護了勞動者和被侵權人,但實際上,其所指向的勞動者工作地法、被侵權人經常居所地法并不一定有利于勞動者或和侵權人。所以,以有利原則取代自眼的沖突規范,是十分必要的。
五、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