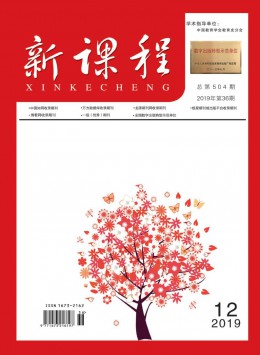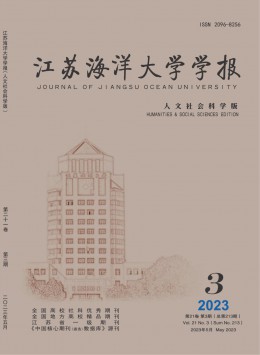表觀遺傳學的意義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表觀遺傳學的意義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是與遺傳學(genetic)相對應的概念,是對經典遺傳學的有益補充;其認為在不改變基因序列的條件下,生物體從基因到基因表型之間存在一種調控,這種機制即“表觀遺傳學”的含義。盡管已被提出70余年,但直到近10余年,隨著科學家們對這種“獲得性遺傳”的進一步認識,才成為生命科學界最熱門的研究之一。因此,研究者們轉換思維,從表觀遺傳學角度對AD發病及治療進行了研究,發現了一系列表觀修飾的關鍵酶類,以及對這些酶類發揮影響的藥物,從而為AD藥物研發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本文擬就AD的表觀遺傳學治療研究綜述如下。
1阿爾茨海默病(AD)概況
阿爾茨海默病(AD)是一種以進行性認知障礙和記憶力損害為主的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它是最常見的癡呆類型,西方國家[中50%?70%的癡呆屬于AD。其病因及發病機制復雜,涵蓋了遺傳和環境的危險因素,涉及成千上萬個基因表達的改變,以及多種信號途徑的上調,如P淀粉樣肽W-amyloidpeptide,Ap)的沉積、Tau蛋白過度磷酸化、炎癥、氧化應激、能量代謝、血管因素及細胞凋亡周期異常等。ad的典型病理改變包括突觸喪失、某些神經遞質水平下降、神經元內異常物質沉積以及選擇性腦神經細胞死亡,使大腦受累區域廣泛萎縮,導致記憶力喪失伴行為改變和人格異常,嚴重者可影響工作及社會生活。受累區域常會出現A沉積、老年斑(senileplaques,SP)、神經原纖維纏結(neurofibrillarytangles,NFT)及Tau蛋白過度磷酸化等。疾病逐漸進展惡化,甚至累及生命。遺憾的是目前尚缺乏延緩或阻礙疾病進展的治療手段。
在AD中,涉及神經元退行性改變的基因達200余個,越來越多的研究數據發現在沒有基因序列改變的情況下,某些機制也可以決定致病基因何時或怎樣表達,最終導致AD發病。因此,AD基因組并不能完全解釋發病機制[14]。已知編碼APP、PSEN1和PSEN2的基因僅可導致家族性早發型AD(early-onsetAD,EOAD);而大多數(約95%)AD均為晚發型AD(late-onsetAD,LOAD)或散發型。因此可以推斷,表觀遺傳現象或環境因素參與了LOAD的致病。這就部分解釋了為什么同一家族中有的家庭成員發病而另一些不發病;而且,在年輕的同卵雙胞胎中基因組無實質上的差異,而在同一老年雙胞胎中其基因表觀遺傳學上存在顯著差異。
大量研究數據證實,基因-環境相互作用在AD的病理生理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營養物質、毒素、環境暴露及人的生活行為,都可以在不改變基因組序列的條件下使基因激活或沉默。目前已知的可調控基因轉錄和表達的表觀遺傳學機制主要分兩大類:①基因選擇性轉錄的調控:包括基因組DNA甲基化,多種組蛋白甲基化及乙酰化等修飾;②基因轉錄后的調控:包括微小RNA(microRNA,miRNA)和小干擾RNA(smallinterferingRNA,siRNA)等非編碼RNA的調節,以及沉默的核糖體RNA(ribosomalRNA,rRNA)基因。除此之外,染色體重塑、基因印記、X染色體失活也屬于表觀遺傳學范疇。
2表觀遺傳學
表觀遺傳學的涵義即在DNA序列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基因的表達與功能發生改變,并產生可遺傳的表型。基本機制即:通過多種基因修飾,影響基因轉錄和(或)表達,從而參與調控機體的生長、發育、衰老及病理過程。至此,表觀遺傳學的發現極大豐富了傳統遺傳學的內容,使人們認識到遺傳信息可以有兩種形式:即DNA序列編碼的“遺傳密碼”和表觀遺傳學信息。它和DNA序列改變不同的是,許多表觀遺傳的基因轉錄和表達是可逆的,這就為許多疾病的治療開創了樂觀的前景。
2.1組蛋白修飾
組蛋白在DNA組裝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利用核心組蛋白的共價修飾傳遞表觀遺傳學信息。這些修飾主要包括組蛋白甲基化、乙酰化、磷酸化、泛素化、ADP-核糖基化及特定氨基酸殘基N-末端的SUMO化;其中組蛋白氨基末端上的賴氨酸、精氨酸殘基是修飾的主要靶點,這些組蛋白翻譯后修飾(post-translationalmodifications,PTMs)對基因特異性表達的調控,是其表觀遺傳學的重要標志。正常機體內,組蛋白修飾保持著可逆的動態平衡。一般而言,組蛋白乙酰化是在組蛋白乙酰轉移酶(histoneacetyl-transferase,HATs)的催化下,從乙酰輔酶A上轉移乙酰基到組蛋白N-末端的賴氨酸殘基上;由于乙酰化中和了組蛋白的正電荷,使組蛋白末端和相關DNA帶負電荷磷酸基團之間的作用減弱,降低了組蛋白和DNA之間的親和力,這種染色質構象的放寬有助于轉錄因子向靶基因片段聚集并利于轉錄的進行。而去乙酰化則是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deacetylases,HDACs)將乙酰基從乙酰化組蛋白轉移到乙酰輔酶A上,形成了致密的染色質狀態,從而使基因轉錄下降或沉默。
2.2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較組蛋白修飾更進一步,是表觀遺傳學的又一重要機制。DNA甲基化主要是在DNA甲基轉移酶(DNAmethyltransferase,DNMTs,包括DNMT1、2、3a/b和4)催化下,將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甲硫氨酸循環中S-腺苷甲硫氨酸(SAM)中的甲基,由四氫葉酸轉移到胞嘧啶的第5位上形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lcytosine,5-mC)。其中,相鄰的胞嘧啶-鳥嘌呤二核苷酸(CpGs)是最主要的甲基化位點。在人類基因組中,CpG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分散存在于DNA中,其CpG70%?90%的位點是甲基化的;另一種CpG呈密集分布于一定區域,稱之為“CpG島”(CpGislands),通常位于或接近基因啟動子區(promoterregions),在正常人體基因組中處于非甲基化狀態。CpG島中的胞嘧啶甲基化可以阻礙轉錄因子的結合,從而可致基因沉默。一般而言,高度甲基化的基因可致表達抑制,而低甲基化的基因可增強基因表達或過表達。
2.3非編碼RNA
表觀遺傳學調控機制涉及RNA的主要包括:miRNA、siRNA以及維持細胞周期的沉默rRNA基因的一部分。
miRNA是較短的雙鏈RNA分子,約有22個核苷酸,來源于機體自身基因即細胞核及細胞質中較大的RNA前體,有自己的啟動子和調控元件。人類基因組中有約700?800個miRNA。這些小分子RNA在轉錄后通過綁定靶mRNA,從而抑制轉錄或誘導mRNA分裂降解。大多數miRNA具有高度保守性和組織特異性,可以調控機體中30%?50%的蛋白質編碼基因。siRNA長短與miRNA相似,作用方式也有很多相同之處,區別在于siRNA可以體外合成,多由外源性導入或感染誘導產生。
重復rRNA基因的復制為真核生物核糖體提供了初始活性位點,在基因表達中是蛋白質合成的熱點區。不同細胞類型可表現不同的活性rRNA比率,提示隨著細胞發育分化,rRNA基因拷貝數比例會發生改變。沉默rRNA的表觀遺傳學方式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活性和非活性rRNAs保持了動態平衡。
2.4染色質重塑、基因印記和X染色體失活
染色質重塑(chromatinremodeling)指基因復制、轉錄和重組等過程中,核小置和結構及其中的組蛋白發生變化,引起染色質改變的過程;主要機制即致密的染色質發生解壓縮,暴露基因轉錄啟動子區中的特定結合位點,使轉錄因子(transcriptionfactor,TF)更易與之結合。基因印記(geneticimprinting)指來自親本的等位基因在發育過程中產生特異性的加工修飾,導致子代體細胞中兩個親本來源的等位基因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即一個等位基因有表達活性,另一等位基因沉默。X染色體失活指雌性哺乳動物細胞中兩條X染色體的其中之一失去活性的現象,即X染色體被包裝成異染色質,進而因功能受抑制而沉默化,使雌性不會因為擁有兩個X染色體而產生兩倍的基因產物。
3AD的表觀遺傳學3.1組蛋白修飾
研究顯示,在AD中存在組蛋白的PTMs。組蛋白3(histone3,H3)磷酸化作為激活有絲分裂的關鍵步驟,可使AD海馬神經元呈過磷酸化狀態。對APP/PS1突變小鼠和野生型小鼠進行條件恐懼訓練,結果顯示前者乙酰化H4較野生小鼠組降低50%;之后對突變組進行HDAC抑制劑(histonedeacetylasesinhibitors,HDACIs)曲古抑菌素A的治療,顯示前者乙酰化H4水平出現了上升。在一項皮層神經元培養模型研究中,APP過度表達則可導致H3和H4乙酰化降低,以及c-AMP反應元件結合蛋白(cAMP-responseelementbindingprotein,CREB)水平下降;而CREB則是腦神經元中激活記憶相關基因,形成長期記憶的關鍵蛋白。總之,盡管在AD患者、AD動物模型及AD培養模型中,都出現了組蛋白修飾,但這個過程是極其復雜的,特異性位點會因功能狀態不同而出現組蛋白乙酰化增加或減少。
3.2DNA甲基化
3.2.1相關基因的甲基化研究顯示,盡管很難判
斷AD中甲基化程度是升高還是下降,但12個甲基化的AD特異性基因表現出了顯著的“表觀偏移”;同時研究還發現,在DNMT1啟動子內一些CpG位點也表現出年齡相關的表觀偏移。研究還發現,葉酸、甲硫氨酸及Hcy代謝與DNA甲基化機制顯著關聯。例如,人類及動物模型葉酸缺乏將導致基因組整體低甲基化,而補充葉酸則可部分逆轉甲基化程度。Smith等研究發現,衰老及AD人群中都出現了葉酸缺乏和甲硫氨酸-Hcy周期的改變。另一研究發現AD患者腦脊液(cerebro-spinalfluid,CSF)中葉酸顯著下降,同樣下降的還有CSF及腦組織中SAM。同時還觀察到AD患者腦組織中S-腺苷同型半胱氨酸(SAH)及血漿中Hcy的升高,后者可抑制DNA甲基化。
目前已知的AD相關基因主要包括:p淀粉樣蛋白前體(APP)基因、早老素1(PS1)和早老素2(PS2)基因、載脂蛋白E(ApoE)基因、p-分泌酶(BACE)基因、sortilin相關受體基因(sortilin-relatedreceptor1gene,SORL1)以及白介素1a(IL-1a)和白介素6(IL-6)基因等。其中,APP基因、BACE基因或PS1基因均存在可調控的CpG甲基化位點。有研究顯示,一例AD尸檢的大腦皮層中APP基因發生了完全去甲基化,而正常樣本或匹克氏病(Pick’sdisease)患者樣本則沒有這種變化。實驗發現,葉酸缺乏所致的BACE和PS1基因表達增強,可通過補充SAM而恢復正常。同樣,體內實驗發現,給予APP過度表達的轉基因小鼠缺乏葉酸、B12及B6的飲食,可以使SAH升高并上調PS1和BACE的表達,以及促進A的沉積和出現認知障礙。在LOAD尸檢標本中,研究者發現了著名的“年齡依賴的表觀遺傳學漂移”(age-dependentepigeneticdrift);對CpG島異常的表觀遺傳學控制,可能促成了LOAD的病理變化,因此,“表觀遺傳學漂移”可能是LOAD個體易感的重要機制。
3.2.2Tau蛋白相關的甲基化Tau蛋白是一種微管結合蛋白(microtubulebindingprotein,MAP),它能與神經軸突內的微管結合,具有誘導與促進微管形成,防止微管解聚、維持微管功能穩定的功能。對記憶和正常大腦功能起重要作用。然而,在AD中,Tau蛋白不僅不再發揮正常功能,還會因異常磷酸化或糖基化等改變了Tau蛋白的構象,使神經元微管結構廣泛破壞,形成以Tau蛋白為核心的NFT,最終導致神經元功能受損或神經元丟失。
人體在正常條件下,Tau蛋白啟動子的AP2結合位點是非甲基化的,但SP1和GCF結合位點則被甲基化。而隨著年齡的增加,SP1作為一種轉錄激活位點甲基化程度升高,GCF作為啟動子抑制位點則逐漸去甲基化,因此總體而言Tau蛋白的基因表達是下調的。尤其在額葉及海馬區域,正常Tau蛋白也出現了年齡相關的下降。蛋白磷酸酶2A(PP2A)是一種針對磷酸化Tau蛋白的去磷酸化酶,PP2A催化亞基的甲基化可以激活該酶。研究顯示,在APP及PS1基因突變的轉基因小鼠中,PP2A的甲基化程度顯著下降,結果顯示Tau蛋白磷酸化增高。對培養的神經元添加葉酸拮抗劑甲氨蝶呤,也可導致PP2A去甲基化,從而增加Tau蛋白的磷酸化程度。另外,還有研究顯示,Hcy可以使PP2A的甲基化程度及活性下降,而添加葉酸和B12則可以逆轉這個過程。總之,Tau蛋白的磷酸化和脫磷酸化間平衡是維持微管穩定性的關鍵因素;而其中磷酸化相關酶類的甲基化程度,成為影響Tau蛋白磷酸化的重要因素。
3.2.3異常的細胞周期和神經元凋亡研究證實,細胞周期異常和神經元凋亡是AD神經退行性變的常見機制。AD神經元中細胞周期及凋亡途徑關鍵因子受DNA甲基化影響并發生上調。包括細胞周期素B2基因、caspase-1基因、caspase-3基因等。這些相關基因的低甲基化使細胞進入異常細胞周期。同樣,高Hcy可使培養神經元凋亡,也間接證實了低甲基化導致異常細胞周期;而使用SAM還可起到拮抗細胞凋亡的效果。
3.3A與miRNA
研究發現,miRNA可以調節APP的表達、APP處理、A聚積以及BACE1的表達,從而導致A毒性改變或影響神經再生。因而,miRNA失調可使APP表達及處理過程發生改變,最終引起神經元存活率和神經再生程度的改變。針對全球AD人群和正常老年人群的對比研究發現,特異性miRNA水平存在顯著差異。研究顯示,在AD中APP相關miRNA顯著下降,而APPmRNA水平則保持平穩,提示miRNA影響APP表達是通過抑制轉錄而不是促進APPmRNA的裂解;同時,在AD皮層中miRNA-106b出現顯著下降。具體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3.4AD與一碳代謝
葉酸代謝又稱為一碳代謝,需要SAM提供甲基。諸多研究表明,AD患者常存在血漿及CSF中Hcy升高(兩者濃度升高常呈正相關),血漿葉酸和B12水平下降,以及腦組織中SAM減少。早期暴露于缺乏葉酸及B族維生素飲食的動物,其AD相關基因在腦組織中發生了表觀遺傳學修飾。SAM作為甲基化過程最重要的甲基來源,其產生及循環依賴于甲硫氨酸循環的正常進行[11]。研究顯示,AD患者CSF中SAM出現顯著下降,口服SAM(1200mg,qd)4?8個月,可以使CSF中SAM濃度升高。同時,維生素B12缺乏可使SAM產生減少,從而影響甲基化。前瞻性隊列研究表明,高Hcy與AD高風險顯著相關,而較高的葉酸攝入量可以降低老年人的AD風險。葉酸缺乏導致的SAM缺乏以及Hcy升高,使甲基化水平下降;并且,Hcy影響SAM和SAH水平,后兩者可調節DNA甲基化活性以及蛋白翻譯后修飾。另外,研究還發現Hcy可通過抑制甲基化,降低PP2A甲基化程度,從而導致Tau蛋白過磷酸化、NFT及SP形成。因此,最關鍵機制即:葉酸/同型半胱氨酸代謝異常導致AD相關基因啟動子的表觀遺傳修飾(CpG區域甲基化狀態的改變),使基因沉默(高甲基化)或過度表達(低甲基化),最終發生AD。
4表觀遺傳學在AD診療中的應用研究
近年來,隨著表觀遺傳學在AD研究中的不斷進步,研究者已逐漸將其應用于AD的診斷及治療中,盡管多數還處于臨床前試驗階段,但表觀遺傳學應用于AD臨床的前景是樂觀并值得期待的。
4.1表觀遺傳學診斷手段
利用亞硫酸氫鈉進行甲基化測序是檢測DNA甲基化的金標準。該方法利用鹽析法從血液中提取基因組DNA,經過亞硫酸氫鹽處理后,變性DNA中胞嘧啶轉換為尿嘧啶,而5-mC則不發生轉換,因此在經過PCR擴增和DNA測序后,胸腺嘧啶則代表非甲基化胞嘧啶,而5-mC(主要為CpG二核苷酸)仍為胞嘧啶。繼而由該方法延伸出多個DNA甲基化分析法,例如:甲基化特異性PCR(methylationspecificPCR,MSP)、結合亞硫酸氫鹽限制性分析(combinedbisulfiterestrictionanalysis,COBRA)以及甲基敏感性單核苷酸引物(methylation-sensitivesinglenucleotideprimerextension,MS-SNuPE)等。然而,由于目前對AD相關基因甲基化的研究還不完善,只能在臨床前研究中應用甲基化測序,用于對比分析AD中基因甲基化的真實狀態。
實時基因成像(real-timegeneticimaging)技術是另一種判斷基因表觀遺傳修飾的手段;該技術避免了尸檢或動物研究,是一種新型的非侵入性的可視化基因調控檢測。磁共振波譜(MRspectroscopy,MRS)即是這樣一種特殊的磁共振成像,該技術可掃描到特定的蛋白,將來可使我們能夠實現對基因表達變化的可視化實時檢測,理論上而言可以追蹤到DNA甲基化或組蛋白修飾的責任蛋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將為AD的表觀遺傳學診斷和治療提供新的手段[39]。
此外,另有研究發現,脂肪酸酰胺水解酶(fattyacidamidehydrolase,FAAH)參與了AD的發病,同時還發現FAAH易于從外周血中檢出,并可作為一個新的潛在的AD生物標志物(biomarker),繼而用于AD的預測或診斷。然而,由于一些AD相關蛋白或酶類在外周血中易降解,穩定的miRNA檢測已成為反映疾病的重要手段。由于大多數AD患者外周血單核細胞中存在各種miRNA的表達上調(如miR-371、miR-517等),且與其在AD腦中高表達相對應,提示通過測定血漿及血單核細胞的miRNA譜變化,可作為AD診斷和病情評估的重要方法。
4.2AD的表觀遺傳學治療
表觀遺傳學對研究AD的發病機制和病程轉歸,以及研發新的藥物等方面開拓了廣闊的空間。表觀遺傳學藥物進入體內后,可充當基因轉錄或表達的“開關”,通過不同的基因修飾及調控基因表觀修飾相關酶類的活性,繼而達到在未改變DNA序列的情況下影響基因表型。因此,正是表觀遺傳學改變的“可逆性”,使與之相關藥物的研發成為AD治療研究的新方向和重點。
4.2.1HDACIs近年來,科學家們研發了多種新的HDACIs。根據化學形態主要分為4類:①短鏈脂肪酸類:如丁酸鈉、苯丁酸鹽和丙戊酸(valproicacid,VPA);②異輕肟酸(hydroxamicacid)類:如曲古抑菌素A(trichostatinA,TSA)、辛二酰苯胺異輕肟酸(suberoylanilidehydroxamicacid,SAHA);③環氧酮類:如trapoxinA和trapoxinB;④苯甲酰胺類:如MS-275。這些HDACIs與鋅依賴性HDAC蛋白(zinc-dependentHDACprotein,I、II及IV類組蛋白亞型)相互作用;煙酰胺作為NAD+前體,可以抑制III類HDAC蛋白。其中,研究最廣泛的是丁酸鈉、苯丁酸鹽、VPA、TSA和SAHA。
目前FDA批準上市的是SAHA,-種治療T細胞淋巴瘤的新型化合物,不僅可增加組蛋白乙酰化水平,同時還可提高認知。在神經系統中,VPA具有抗驚厥和穩定情緒的作用,因此這些作用可能與引起組蛋白乙酰化改變有關;VPA還可以通過抑制GSK-3#介導的y-分泌酶裂解APP,從而抑制Ap的產生,減少A斑塊,最終緩解AD模型鼠的認知功能障礙。Ricobaraza等研究顯示,4-苯基丁酸乙酯(PBA)可通過降低GSD-3#來降低AD大鼠腦內Tau蛋白磷酸化,并可清除突觸間A沉積,減輕內質網壓力,從而恢復記憶并逆轉學習障礙。而煙酰胺則可選擇性降低Tau蛋白磷酸化并增加乙酰化的a微管蛋白。Fischer等也研究發現,非特異性HDACIs如VPA、TSA、4-苯基丁酸鈉及伏立諾他等,都可以通過不同的表觀遺傳機制影響Ap沉積和Tau蛋白過磷酸化,并可改善學習和記憶力。另外,HDACi丙戊酸可以降低APP的表達,減輕大腦中的A肽斑塊負擔;研究還證實,HDACI治療還可誘導樹突發芽,增加突觸數量,以及恢復學習行為和形成長期記憶。Zhang等報道,口服HDACIMS-275可改善神經炎癥和腦淀粉樣變,以及改善AD模型動物的行為能力。這些研究提示,HDACIs可通過調節HDAC蛋白活性和Tau蛋白磷酸化水平,從而用于AD的治療.
HDACIs可選擇性抑制HDACs,導致組蛋白乙酰化水平升高,恢復AD模型動物中組蛋白乙酰化水平及提高學習和記憶能力。例如:Guan等發現當腦內HDAC2過表達時,小鼠海馬神經元樹突棘密度降低、突觸形成減少、CA1區LTP形成障礙、空間記憶和工作記憶損傷;而使用HDACIs則能夠促進小鼠神經元樹突棘和突觸的形成,改善AD模型小鼠的學習和記憶減退狀態。因此,HDAC2可能是HDACIs最適宜的治療靶點之一,可能使腦神經元內合成新的蛋白以改善或恢復AD患者記憶。除此之外,HDACIs對基因表達的調節具有特異效應,可以在上調靶基因表達的同時下調其他基因;這種基因特異性常通過轉錄因子來調控,后者可以識別特定啟動子和增強子序列,并賦予靶基因特異性(gene-specificeffects),使之對HDACIs具有敏感性[44],繼而逆轉表觀遺傳改變。同時,應用HDACIs治療AD還應當考慮其是否可穿透血腦屏障,因此,最近的一項研究研發了一種可進入CNS(“CNS-penetrant”)的HDACIs(I類)EVP-0334,目前已進入I期臨床試驗用于AD治療。
眾所周知,AD大腦受累的主要區域為內側嗅皮質、海馬及杏仁核等。研究發現,與正常腦組織相比,AD患者皮質中HDAC6蛋白水平升高了52%,而海馬中則升高了92%。HDAC6與Tau蛋白共同存在于核周,并發生相互作用;其中HDAC6具有獨立的微管蛋白脫乙酰基酶的活性。使用HDAC6抑制劑Tubacin治療或敲除HDAC6,并不能影響HDAC6與Tau蛋白的相互作用,但可以減少Tau蛋白磷酸化[55]。通過結合HDAC6,Tau蛋白可抑制脫乙酰酶活性,從而導致微管蛋白乙酰化增加;在Tau蛋白過表達的細胞中也可見這種增加;說明過量的Tau蛋白成為HDAC6的抑制劑,然而AD患者中正常Tau蛋白是減少的。文獻顯示,HDAC6的減少或丟失可改善聯想和空間記憶形成[56,57],以及阻斷A誘導的海馬神經元線粒體運輸障礙。最近有研究人員還發現,HDAC6無效突變(nullmutation)可以挽救神經元中Tau蛋白誘導的微管缺陷。他們采用遺傳和藥理學方法抑制HDAC6的tubulin特異性脫乙酰基酶活性,證實這種“挽救效應”有可能是通過增進微管乙酰化所介導的。這些研究結果表明,HDAC6有可能是AD和相關Tau病的一種獨特的有潛力的藥物靶點,HDAC6抑制劑有望成為AD治療的新型藥物。
目前研究證實,HDACIs可用來治療神經變性病、抑郁、焦慮情緒、認知功能障礙及神經發育障礙,因此為AD的治療提供廣闊的前景。但現有的HDACIs存在生物利用度低、代謝快、低選擇性等缺點。因此,研究開發結構新穎、副作用小、特異性及選擇性高的HDACI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4.2.2飲食因素除此之外,飲食因素,例如葉酸、維生素B2、B6、B12、蛋氨酸、膽堿等都可以影響甲基供體SAM的形成,并影響DNMTs活性;同時,一些天然化合物,如異黃酮、黃酮、兒茶素、姜黃素、白藜蘆醇等,可以改變表觀遺傳學機制,影響染色質修飾酶的活性,因此備受關注。
研究證實,傳統用于抗腫瘤、抗氧化、抗炎、抗細胞凋亡及預防高脂血癥的姜黃素,也可用于治療AD:在體外實驗中,姜黃素可抑制A聚集沉積、A#誘導的炎癥、戶分泌酶及乙酰膽堿酯酶的活性;而體內實驗則證實,口服姜黃素可抑制AD動物腦組織中Ap沉積、Ap寡聚化及Tau蛋白磷酸化,并改善行為及認知。另有研究發現,姜黃素還可加速淀粉樣斑塊的分解,繼而改善AD的空間記憶障礙。據Bora-Tatar等[65]報道,在33種羧酸衍生物中,姜黃素是最有效的HDAC抑制劑,甚至比丙戊酸和丁酸鈉更強效;另有研究也發現,姜黃素可顯著降低HDAC1、3和8蛋白水平,并可提高乙酰化H4水平。同時,姜黃素還是潛在的HAT抑制劑,2004年Balasubramanyam等[66]發現,姜黃素是p300/CREB結合蛋白HAT活性特異性抑制劑,對維持一定的CREB水平起到關鍵作用。因此,姜黃素對HDAC和HAT均有調節作用;作為已知的抗氧化劑,姜黃素可能是通過調節氧化應激,從而對乙酰化和去乙酰化具有雙重調節作用。
AD表觀遺傳學改變受環境、營養因素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因此自孕前保健開始,直至子代的一生,都保持機體內外生存環境的良好,保證表觀遺傳學正常修飾及表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預防AD的發生。同時,由于目前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等都是公認的AD高危因素,通過表觀遺傳學機制防治這些疾病,也是降低AD的發生風險的重要手段。另外,提倡低熱量、低膽固醇和富含葉酸、B族維生素及姜黃素等的飲食,以及降低血漿Hcy值,可能對保護大腦神經元,改善老年期認知,以及預防AD發生或逆轉AD的表觀遺傳改變,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4.2.3其他因素由于DNA甲基化是可逆的,該過程的相關酶類也可作為AD治療的研究靶點,例如DNMT抑制劑。然而,目前對DNMT抑制劑的研究多局限于腫瘤的治療,因此對于AD的治療作用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研究發現AD中與APP裂解機制相關的多個miRNA也發生了改變,因此針對miRNA的AD表觀遺傳治療成為重要研究方向。2006年,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裴鋼院士研究組研究發現,腎上腺素受體被激活后,可以增強y-分泌酶的活性,進而能夠增加AD中Ap的產生。這項發現揭示了AD致病的新機制,提示腎上腺素受體有可能成為研發AD治療藥物的新靶點。
5展望
綜上所述,在AD中,表觀遺傳學機制對疾病發生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尤其是散發性AD。表觀遺[8]傳學調節障礙導致相關基因轉錄異常,引起關鍵蛋白或酶類異常,繼而發生一系列病理生理改變,是AD發病的主要原因。表觀遺傳學改變可以通過表觀遺傳藥物進行逆轉,因而這不僅為AD的治療開創了一片新天地,更引導醫藥行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然而,使用表觀遺傳學藥物治療疾病也面臨著一系列難題。對于目前可用的表觀遺傳學化合物如HDACIs及辣椒素等而言,主要的困難即缺乏針對不同腦區、不同神經元亞型或特異基因的“選擇性”。
第2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1 DNA甲基化和組蛋白乙酰化
1.1 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復制以后,在DNA甲基化酶的作用下,將S-腺苷甲硫氨酸分子上的甲基轉移到DNA分子中胞嘧啶殘基的第5位碳原子上,隨著甲基向DNA分子的引入,改變了DNA分子的構象,直接或通過序列特異性甲基化蛋白、甲基化結合蛋白間接影響轉錄因子與基因調控區的結合。目前發現的DNA甲基化酶有兩種:一種是維持甲基轉移酶;另一種是重新甲基轉移酶。
1.2 組蛋白乙酰化 染色質的基本單位為核小體,核小體是由組蛋白八聚體和DNA纏繞而成。組蛋白乙酰化是表觀遺傳學修飾的另一主要方式,它屬于一種可逆的動態過程。
1.3 DNA甲基化與組蛋白乙酰化的關系 由于組蛋白去乙酰化和DNA甲基化一樣,可以導致基因沉默,學者們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串擾現象。
2 表觀遺傳學修飾與惡性腫瘤耐藥
2.1 基因下調導致耐藥 在惡性腫瘤中有一些抑癌基因和凋亡信號通路的基因通過表觀遺傳學修飾的機制下調,并與化療耐藥有關。其中研究比較確切的一個基因是hMLH1,它編碼DNA錯配修復酶。此外,由于表觀遺傳學修飾造成下調的基因,均可導致惡性腫瘤耐藥。
2.2 基因上調導致耐藥 在惡性腫瘤中,表觀遺傳學修飾的改變也可導致一些基因的上調,包括與細胞增殖和存活相關的基因。上調基因FANCF編碼一種相對分子質量為42000的蛋白質,與腫瘤的易感性相關。2003年,Taniguchi等證實在卵巢惡性腫瘤獲得耐藥的過程中,FANCF基因發生DNA去甲基化和重新表達。另一個上調基因Synuclein-γ與腫瘤轉移密切相關。同樣,由表觀遺傳學修飾導致的MDR-1基因的上調也參與卵巢惡性腫瘤耐藥的形成。
3 表觀遺傳學修飾機制在腫瘤治療中的應用
3.1 DNA甲基化抑制劑 目前了解最深入的甲基化抑制劑是5-氮雜脫氧胞苷(5-aza-dc)。較5-氮雜胞苷(5-aza-C)相比,5-aza-dc首先插入DNA,細胞毒性比較低,并且能夠逆轉組蛋白八聚體中H3的第9位賴氨酸的甲基化。有關5-aza-dc治療卵巢惡性腫瘤的體外實驗研究結果表明,它能夠恢復一些沉默基因的表達,并且可以恢復對順柏的敏感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hMLH1基因。有關地西他濱(DAC)治療的臨床試驗,研究結果顯示,結果顯示:DAC是一種有效的治療耐藥性復發性惡性腫瘤的藥物。 轉貼于
3.2 HDAC抑制劑 由于組蛋白去乙酰化是基因沉默的另一機制,使用HDAC抑制劑(HDACI)是使表觀遺傳學修飾的基因重新表達的又一策略。根據化學結構,可將HDACI分為短鏈脂肪酸類、氯肟酸類、環形肽類、苯酸胺類等4類。丁酸苯酯(PB)和丙戊酸(VPA)屬短鏈脂肪酸類。PB是臨床前研究最深入的一種HDACI,在包括卵巢惡性腫瘤在內的實體腫瘤(21例)Ⅰ期臨床試驗中有3例患者分別有4~7個月的腫瘤無進展期,其不良反應是短期記憶缺失、意識障礙、眩暈、嘔吐。因此,其臨床有效性仍有待于進一步在Ⅰ、Ⅱ期臨床試驗中確定。在VPA的臨床試驗中,Kuendgen等在對不同類型血液系統腫瘤中使用VPA進行了Ⅱ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不同的患者有效率差異甚遠。辛二酰苯胺異羥肟酸(SAHA)是氯肟酸類中研究較深入的一種HDACI。其研究表明,體內使用安全劑量SAHA時,可有效抑制生物靶點,發揮抗腫瘤活性。大量體外研究結果顯示,聯合使用DNA甲基化抑制劑和HDACI會起到更明顯的協同作用。
3.3 逆轉耐藥的治療 Balch等使用甲基化抑制劑—5-aza-dc或zebularine處理卵巢惡性腫瘤順柏耐藥細胞后給予順柏治療,發現此細胞對順柏的敏感性分別增加5、16倍。在臨床試驗中,Oki等將DAC和伊馬替尼(imatinib)聯合使用治療白血病耐藥患者,結果說明,應用表觀遺傳學機制治療惡性腫瘤確實可以對化療藥物起到增敏作用,并且在一定范圍內其療效與體內表觀遺傳學的改變呈正比。Kuendgen和Pilatrino等對HDACI和化療藥物的給藥順序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在使用VPA達到一定血清濃度時加用全反式維甲酸可增加復發性髓性白血病和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患者的臨床緩解率,這可能與VPA引起的表觀遺傳學改變增加患者對藥物的敏感性有關。
4 展望
總的來說,應用表觀遺傳學修飾機制治療腫瘤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與傳統化療藥物聯合來逆轉耐藥,將給攻克惡性腫瘤等疾病帶來新的希望。
參 考 文 獻
第3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摘要:目的:觀察愈肝顆粒對大鼠肝癌模型的防治作用,并進一步探討其表觀遺傳學機制。方法:采用甲基化特異性PCR(methylationspecificPCR,MSP)技術檢測大鼠肝組織p16抑癌基因異常甲基化情況,RT-PCR法檢測3種主要DNA甲基轉移酶(DNMT1、DNMT3A、DNMT3B)水平變化,ELISA法檢測血清AFP水平,HE染色觀察肝臟病理情況。結果:HE染色顯示愈肝顆粒組大鼠肝臟病理改變較輕,細胞異形性不明顯,而模型對照組大鼠肝臟細胞異形性明顯,癌細胞排列呈梁狀或多板狀或實性成片排列。結論:愈肝顆粒可對大鼠肝癌的發生有防治作用,其機制與調節DNMTs表達水平及調整p16抑癌基因基因啟動子甲基化水平有關。
關鍵詞:愈肝顆粒;大鼠;肝癌;二乙基亞硝胺;DNA甲基轉移酶;p16基因;甲基化
中圖分類號:R735.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197(2008)10-0026-02
原發性肝癌是臨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盡管近年來肝癌在診治有很大進展,但其預后仍不樂觀,因此采取預防措施降低其發生顯得尤為重要。中藥在防治肝癌方面有廣闊的前景。本課題旨在通過動物試驗,制造肝癌模型,運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觀察愈肝顆粒對DNMTs、p16抑癌基因基因啟動子甲基化水平的影響,探索愈肝顆粒防治肝癌的作用機理,為臨床防治肝癌提供可靠的實驗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1試驗材料與儀器
RNA抽提試劑盒(Trizol試劑盒)及DNA抽提試劑盒均購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大鼠p16基因甲基化檢測試劑盒購自上海杰美基因醫藥科技有限公司;RT試劑盒購自東洋紡(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PCR試劑盒購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瓊脂糖凝膠購自西班牙DIOWEST公司;DNAMarker購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大鼠(rat)甲胎蛋白(AFP)檢測試劑盒購自美國ADL公司;二乙基亞硝胺(DEN)購自sigma公司,愈肝顆粒浸膏由瀘州市中醫院制劑室生產,主要成分由茵陳、梔子、黨參、黃芪、白術、青皮、丹參、澤蘭、茜草等13味中藥組成,SD大鼠由瀘州醫學院動物試驗中心提供。
1.2方法
1.2.1動物模型制作及分組
選用標準清潔級SD大鼠70只,體重180±30g,將其隨機分至3組,空白對照組10只,模型對照組30只,愈肝顆粒組30只,每組均為雌雄各半。模型對照組、愈肝顆粒組大鼠腹腔注射40mg/kg體重的DEN,2次/周,連續8周。空白對照組則注射等體積的生理鹽水。同時,自實驗開始愈肝顆粒組大鼠給予愈肝顆粒浸膏(每毫升相當于原生藥1.86g)灌胃,10mL/kg體重,每天一次,連續8周。模型對照組、空白對照組大鼠給予等體積生理鹽水灌胃,8周末處死動物,留取標本。
1.2.2RT-PCR檢測
采用Trizol法提取肝組織RNA,NanoDorpND-1000核酸蛋白測定儀定量,-70℃冰箱保存。每個樣本設40μL反應體積,將2μg總RNA為底物及2μL隨機引物、2μL逆轉錄酶、4μLdNTPs、1μLRNaseInhibitor42℃反應20min,cDNA于-20℃冰箱保存。以各樣本cDNA5μL為模板,引物對按前向、反向順序排列為:DNMT1:5′-CTGAGGAAGGCTACCTGGCTAA-3′,5-TGTCCGACTTGCTCCTCCTG-3′,擴增片段204bp,DNMT3A:5′-GGAATGTGCCAGAACTGTAAGA-3′,5′-CCTGTAGCAATCCCATCAAA-3′,擴增片段404bp,DNMT3B:5′-TGGTGAAGCGGATGATGGAGATGGC-3′,5′-CCGATGGCGTACTGCTGCTCTTAGG-3′,擴增片段329bp,GAPDH:5′-AAATCCCATCACCATCTTCC-3′,5′-CCTGCTTCACCACCTTCTTG-3′,擴增片段581bp。
PCR反應體系:逆轉錄反應后原液2.5μL,Primer1(10μM)1μL,Primer2(10μM)1μL,2×MasterMix12.5μL,反應體積25μL。反應循環的設置:94℃3min;94℃30sec,TM℃30sec,72℃1min,30循環;72℃延伸5min。以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lyceraldehyde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H)為內參照。2%-3%瓊脂糖凝膠電泳,凝膠成像系統進行半定量分析以目的基因條帶與內參照GAPDH基因條帶吸光度值進行比較,計算其比值,并對實驗分組中各樣本計算結果取均值(見表1)。
表1各組大鼠肝組織中MSP與DNMTs的表達情況
(±s)
注:與空白對照組比較,P
1.3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3.0進行統計分析。數據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計量資料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規定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HE染色光鏡下觀察結果(見圖1-6)
空白對照組(圖1,2):肝細胞以中央靜脈為中心呈放射狀排列,大小均一,細胞核大而圓,胞質豐富。模型對照組(圖3,4):癌細胞排列呈梁狀、索狀或不規則。愈肝顆粒組(圖5,6):細胞排列基本規則,異形性不明顯。
2.2p16基因異常甲基化
24例模型對照組大鼠肝臟標本經MSP法檢測,18例p16基因啟動子區異常甲基化(18/24),26例愈肝顆粒組大鼠肝臟標本MSP檢測,p16基因啟動子區異常甲基化(16/26),而10例空白對照組大鼠肝組織檢測均為陰性(圖7)(備注:造模死亡10只大鼠)。
圖7p16基因啟動子區甲基化MSP檢測結果
2.3DNNMTs半定量結果
采用優化RT-PCR反應條件,對各個樣本cDNA以特定引物(DNNMTs)及內參照GAPDH引物進行擴增,表1顯示為半定量結果。
3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24例模型對照組大鼠肝臟標本經MSP法檢測,18例p16基因啟動子區異常甲基化(18/24),26例愈肝顆粒組大鼠肝臟標本MSP檢測,p16基因啟動子區異常甲基化(16/26),而10例空白對照組大鼠肝組織檢測均為陰性,說明p16基因的失活在肝癌的發生中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表明愈肝顆粒可能通過抑制DNA的甲基化作用防治肝癌。模型對照組和愈肝顆粒組大鼠肝組織DNMTs水平檢測結果與空白對照組比較,p16基因異常甲基化陽性組DNMT3A、DNMT3B升高較明顯而DNMT1則相對下降,表明DNMT3A、DNMT3B在促進p16基因異常甲基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同時表明3種DNMTs相對水平改變及相互作用與此進程關系密切;與Kimura等在腎透明細胞癌中的研究結果不同的是,DNMT1在MSP陰性的肝癌組織中高于正對照組并略高于異常甲基化陽性組。檢測26例愈肝顆粒組與24例模型對照組大鼠肝組織DNMT1、DNMT3A、DNMT3B水平,結果顯示:前者三項水平均較后者低,差異明顯,均P
參考文獻:
第4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硒 表觀遺傳修飾 表觀標志物抑制劑 抗癌藥 開發
中圖分類號:R97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33(2017)03-0075-04
Selenium compounds ― looking forward to be developed as epigenetic targeting selenium-containing anti-tumor drugs*
ZHU Huiqiu1**, HUA Yan1, WANG Mingli2***
(1. Anhui Huaxin Pharmaceutical Co. Ltd., Hefei 230000, China; 2.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 Selenium compounds can produce an intervention effect on the abnormality of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and then repress the oc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 tumor. They can be used as the inhibitors of some tumor specific epigenetic markers and expected to be developed as a new type of epigenetic targeting selenium-containing anti-tumor drugs.
KEy WORDS selenium; epigenetic modification; inhibitors of epigenetic markers; anti-cancer drugs; development
硒最重要的生物學功能是抗癌,并以多種機制發揮其抗癌作用。近年來的研究發現,硒又可對表觀遺傳學調控機制異化產生干預影響,特別是對在腫瘤發生機制中的特異性靶點進行干預,進而阻抑腫瘤的發生及轉移。硒化物是某些腫瘤特異性表觀標志物有效的抑制劑。硒的這個功能不僅對臨床腫瘤診斷、治療、預防具有現實意義,更為“含硒表觀靶向抗癌藥物”開發提供了科學依據。“含硒表觀靶向抗癌藥物”是期待開發的新型抗癌藥。現就近些年在這些方面的相關研究作一簡要介紹。
1 表觀遺傳學
什么是表觀遺傳學?從孟德爾遺傳規律講,親代(一代)把遺傳信息傳遞給子代(二代),主要由攜帶遺傳信息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分子中堿基的排列順序(即堿基序列)來決定,并在細胞核內遺傳。但人們在研究中發現,在DNA堿基序列以外還有一套調控機制,包括 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染色質重塑以及非編碼RNA等,它們在不涉及改變DNA堿基序列的情況下,影響轉錄活性并調控基因的表達,改變機體的性狀,并且是一種可以預和逆轉的遺傳機制。這種非孟德爾遺傳現象,稱作表觀遺傳學[1-2]。
2 硒對表觀遺傳修飾異常產生干預及逆D作用
腫瘤發生發展的主要生物學原因是原癌基因活化和抑癌基因失活[3]。研究顯示,DNA甲基化水平同這些基因的表達密切相關。通常情況下,甲基化水平同基因表達呈負相關,甲基化程度越高,基因表達活性越低,甲基化程度越低,基因表達越活躍[4]。
DNA甲基化主要表現為基因組整體甲基化水平降低和局部CpG島[在哺乳動物中富含胞嘧啶-磷酸-鳥嘌呤(CpG)二核苷酸的一段DNA稱為CpG島]甲基化程度的異常升高,人類基因組的甲基化主要發生在CpG島[5]。
研究表明,實體瘤普遍存在基因組廣泛低甲基化現象,低甲基化使原癌基因活化,癌細胞異常增殖;低甲基化還使腫瘤轉移增加,例如胃癌的甲基化水平越低,癌細胞浸潤、轉移的傾向越明顯[6]。
CpG島的甲基化程度異常升高,會導致某些抑癌基因表達沉默,進而參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在正常情況下,CpG島為非甲基化。當腫瘤抑癌基因的啟動子區域(CpG島)過度甲基化,就會使抑癌基因的表達沉默。其間DNA甲基轉移酶(DNMT)家族中的DNMT1發揮著重要的調控作用,它的高表達導致抑癌基因在CpG島失活。所以,CpG島高甲基化成了多種腫瘤特異性表觀標志物,已成為臨床多種腫瘤早期診斷的依據和指標[7]。
近年來,作為表觀遺傳學調控機制之一的組蛋白修飾在腫瘤研究領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組蛋白乙酰化由組蛋白乙酰轉移酶(HAT)和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共同調控,而編碼HAT或HDAC的基因如果發生染色體易位、擴增等突變會導致某些腫瘤的發生。
可見,DNA甲基化和組蛋白乙酰化等表觀遺傳修飾異常是腫瘤發生的另外一個機制。而近年研究發現,硒通過靶向干預可逆轉甲基化和乙酰化異常的過程,從而抑制腫瘤的發生及轉移。硒化物成了潛在的治癌新藥物,是亟待開發、臨床應用前景可觀的“含硒表觀靶向抗癌藥物”。
2.1 硒對DNA甲基化產生干預作用
研究表明,膳食硒通過干預表觀遺傳過程顯示出其抗癌潛力,膳食缺硒時組織呈現整體低甲基化[8]。Davis等[9]早些時候研究發現,給大鼠喂食缺硒膳食,其肝臟和結腸都出現顯著DNA低甲基化,而經硒處理的人結腸癌細胞株Caco-2 DNA甲基化水平顯著高于未經硒處理的對照組,據此研究者認為,膳食缺硒會增加肝臟和結腸腫瘤的發生。Remely等[8]研究表明,膳食硒營養缺乏會引起動物組織和人體結腸癌DNA低甲基化。我國學者徐世文等[4]通過實驗也發現,飼料硒缺乏可導致雞肌肉組織 DNA甲基化水平降低。硒對DNMT有抑制作用,缺硒會導致DNMT活性增加,使原癌基因活化,引起結腸癌等多種腫瘤發生。保持硒等營養素均衡攝入,有利于維持DNA甲基化正常水平及抑制DNMT活性[6]。
CpG島DNMT1的高表達是使抑癌基因失活的重要機制。抑制DNMT1靶酶活性,使失活的抑癌基因復活,是腫瘤治療中探索的新途徑。硒在多種腫瘤中有去甲基化的生物學功能,能誘導失活的抑癌基因重新活化和表達[3]。研究發現,硒可以直接干預DNA甲基化,抑制腺癌細胞株DNMT的高表達[8]。膳食硒干預DNA甲基化的方式之一是通過去甲基化過程來調節DNMT1活性的;研究還證實,亞硒酸鈉和苯甲基氰酸硒(BSC)、1,4-苯雙(亞甲基)氰酸硒(p-XSC)兩種合成硒化物對人大腸癌細胞核提取物中DNMT的活性都有抑制作用[10]。
各方面的研究驗證,硒對DNA甲基化產生干預影響,是靶酶DNMT有效的抑制劑。
2.2 硒干預影響組蛋白的乙酰化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研究發現,組蛋白去乙酰化酶與腫瘤的發生密切相關。HDACs家族中的HDAC1高表達可明顯增加腫瘤細胞的增殖能力。在食管鱗癌、前列腺癌等多種腫瘤中均發現HDAC的高表達,靶酶HDAC已成為首選的攻擊靶點。
目前,人們通過體內、體外的研究鑒定出了硒、丁酸鹽、曲古抑菌素A(TSA)等一些HDAC的抑制劑,這些抑制劑可在體外誘導多種腫瘤細胞的生長停滯、分化或凋亡[2]。Somech等[11]通過臨床試驗表明,HDAC抑制劑對人體白血病及實體瘤進行治療,表現出明顯的抗腫瘤增殖效果,研究者認為,各類HDAC抑制劑是另一類新型抗癌藥物、“癌癥治療的新工具”。
Xiang等[12]的研究證明,硒可以通過下調DNMT和抑制HDAC活性,活化人前列腺癌LNCaP細胞系中因高甲基化沉默的基因GSTP1, APC和CSR1。這些基因是具有保護免受氧化損傷的抗癌活性物質、化學致癌物解毒劑或腫瘤抑制劑。
甲基硒酸(MSA)是近年來新研制成的一種人工低分子量有機硒化合物,是很具潛力的抗癌制劑。Kassam等[13]通過對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細胞系(DLBCL)w外研究首次發現,MSA可以抑制該細胞系HDAC的活性。研究者認為,有關MSA抑制HDAC活性的作用以前從未報道過,從而為人們提供了硒元素一種新的機制,MSA是日后臨床試驗中可以使用的硒化物。
我國科研人員胡琛霏[2]通過蛋白質免疫印跡的方法,檢測到MSA可抑制食管鱗癌細胞系HDAC的活性,降低HDACl和HDAC2的蛋白表達,引起細胞內組蛋白乙酰化水平顯著升高;同時,還檢測到硒甲硫氨酸(SLM)對食管鱗癌細胞系KYSEl50細胞和MCF7細胞的作用,在SLM處理細胞24 h后,細胞中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活性也顯著降低。
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含硒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被發現和驗證。亞硒酸鈉、酮C甲基硒丁酸鹽(KMSB)、甲基硒代半胱氨酸(MSC)、甲基硒丙酮酸(MSP)等硒化物都可以抑制HDAC活性,提高組蛋白乙酰化水平,作為潛在的HDAC抑制劑,發揮其抗腫瘤的作用[14]。Fernandes 等[15]介紹,KMSB 和 MSP在體外作為HDAC的競爭性抑制劑發揮抗癌作用;還報道,合成的SAHA含硒類似物(5-苯甲酰戊氰硒)二硒醚和5-苯甲酰戊氰硒對不同肺癌細胞株HDAC抑制效果比SAHA更好。SAHA是氧肟酸類HDAC抑制劑,是目前在臨床上以皮膚T淋巴細胞瘤(CTCL)為適應癥而廣泛應用的表觀靶向抗癌藥物。這也提示,含硒類抑制劑對靶酶HDAC抑制效果優于無硒類抑制劑。
為何上述各種硒化物都可靶向抑制DNMT和HDAC活性,研究發現不管其結構如何改變,硒都是這些化合物生物活性的中心元素,發揮著關鍵作用,硒的這一生物學功能對含硒抗癌藥物的開發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6]。
2.3 硒對非編碼RNA調控機制產生干預效應
表觀遺傳學的一個重要調控機制是非編碼RNA。非編碼RNA是指不能翻譯為蛋白質的RNA分子。近年來,非編碼RNA一族中的微小RNA-200(miR-200)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研究發現,miR-200家族中的成員微小RNA-200a(miR-200a)與腫瘤的發生發展關系密切,miR-200a在腫瘤組織中呈現明顯低表達。因此,miR-200a的表達下調是腫瘤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miR-200a也成了腫瘤特異性表觀標志物[17]。
胡琛霏[2]通過TaqMan芯片,檢測了MSA處理食管鱗癌細胞后細胞中微小RNA(miRNA)的變化情況,發現MSA可以上調細胞中miR-200a 的表達水平,miR-200a 表達升高后,負性調控Kelch樣環氧氯丙烷相關蛋白-1(Keap1)的表達,使Keap1蛋白水平下降,上調轉錄因子NF-E2相關因子2(Nrf2)蛋白水平并提高其轉錄活性(Nrf2活性受其細胞質接頭蛋白Keap1的調控),從而活化Keap1-Nrf2信號通路。而Keap1-Nrf2信號通路在抗氧化、預防腫瘤發生等諸多方面有重要作用[18]。
體外研究顯示[19] ,人腦膜瘤組織中miR-200a表達明顯低于正常組織,β-循環蛋白(β-catenin)和其下游靶基因細胞周期蛋白D1表達顯著增高,二者和miR-200a呈現負相關,上調miR-200a可降低β-catenin的表達,進而阻斷Wnt/β-catenin信號傳導通路來抑制腦膜瘤的生長。胡琛霏課題組前期研究也發現MSA可以抑制食管鱗癌細胞系中β-catenin的表達[2] 。研究已證實,Wnt/β-catenin信號通路的激活和高表達可促進腫瘤細胞的增殖、侵襲、轉移及抑制腫瘤細胞的凋亡[20]。
由此可見,MSA可能介導、調控著miR-200a表達及參與復雜的分子調控網絡,從而抑制腫瘤發生及轉移。
3 展望
加強硒與表觀遺傳學之間關聯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生物醫學意義。它有可能解釋硒化學抗腫瘤的新機制,從理論上證明硒元素可能具有表觀遺傳學的效應[21] 。綜上所述,硒在腫瘤形成中對表觀遺傳修飾異常產生干預影響,靶向抑制腫瘤特異性表觀標志物,逆轉表觀遺傳修飾發生異化過程,使我們認識了硒化學抗癌的新機制、新作用,硒化物是潛在開發的新型靶向抗癌藥物。Fernandes 等[15]指出,硒化物都是癌癥治療藥。目前,非表觀類含硒靶向抗癌藥如硒唑呋喃、依布硒啉、乙烷硒啉等早已進入臨床研究[16],展示出很有希望的臨床應用前景。而含硒表觀靶向抗癌藥物是亟待開發的抗癌藥“富礦”,加快開發含硒表觀靶向抗癌藥物,可為臨床腫瘤治療增加一種“新的工具”,為癌癥患者戰勝病魔增添一份新的希望。人們熱切期盼“含硒表觀分子靶向抗癌藥物”早日問世。
致謝:本課題研究得到華中科技大學徐輝碧、黃開勛兩位教授和安徽醫科大學張文昌碩士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參考文獻
[1] 王杰, 徐友信, 刁其玉, 等. 非孟德爾遺傳模式: 表觀遺傳學及其應用研究進展[J]. 中國農學通報, 2016, 32(14): 37-43.
[2] 胡琛霏. 甲基硒酸調控食管鱗癌細胞表觀遺傳改變的機制研究[D]. 北京: 北京協和醫學院, 中國醫學科學院, 2014.
[3] 華巖. 硒?生命的營養素[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97-98.
[4] 徐世文, 蔣智慧, 王超, 等. 硒缺乏對雞肌肉組織DNA甲基化水平的影響[J]. 東北農業大學學報, 2012, 43(9): 42-46.
[5] 陸嶸, 房靜遠. 表觀遺傳修飾與腫瘤[J]. 生命科學, 2006, 18(1): 10-14.
[6] 騰麗娟, 張長松, 李克. 營養與腫瘤表觀遺傳學關系的研究進展――DNA甲基化機制[J]. 醫學研究生學報, 2008, 21(1): 95-97.
[7] 尹惠子, 單明, 尤子龍, 等. 腫瘤發生過程中表觀遺傳學機制――DNA甲基化的研究進展[J]. 實用腫瘤學雜志, 2015, 29(2): 173-177.
[8] Remely M, Lovrecic L, de la Garza AL, et al. Therapeutic perspectives of epigenetically active nutrients[J]. Br J Pharmacol, 2015, 172(11): 2756-2768.
[9] Davis CD, Uthus EO, Finley JW. Dietary selenium and arsenic affect DNA methylation in vitro in caco-2 cells and in vivo in rat liver and colon[J]. J Nutr, 2000, 130(12): 2903-2909.
[10] Speckmann B, Grune T. Epigenetic effects of selenium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health[J]. Epigenetics, 2015, 10(3): 179-190.
[11] Somech R, Izraeli S, J Simon A.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new tool to treat cancer[J]. Cancer Treat Rev, 2004, 30(5): 461-472.
[12] Xiang N, Zhao R, Song G, et al. Selenite reactivates silenced genes by modifying DNA methylation and histones in prostate cancer cells[J]. Carcinogenesis, 2008, 29(11): 2175-2181.
[13] Kassam S, Goenaga-Infante H, Maharaj L, et al. Methylseleninic acid inhibits HDAC activity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cell lines[J]. Cancer Chemother Pharmacol, 2011, 68(3): 815-821.
[14] Rajendran P, Ho E, Williams DE, et al. Dietary phytochemicals, HDAC inhibition, and DNA damage/repair defects in cancer cells[J/OL]. Clin Epigenetics, 2011, 3(1): 4. doi: 10.1186/1868-7083-3-4.
[15] Fernandes AP, Gandin V. Selenium compounds as therapeutic agents in cancer[J]. Biochim Biophys Acta, 2015, 1850(8): 1642-1660.
[16] 寶泉, 史艷萍, 李彩文, 等. 基于硒元素的抗癌藥物研究進展[J]. 化學通報, 2011, 74(8): 709-714.
[17] 汪建林, 楊西勝, 李小磊, 等. miR-200a與腫瘤關系[J].現代腫瘤醫學, 2013, 21(12): 2853-2856.
[18] 殷園園, 武夏芳, 武端端, 等. 核因子E2相關因子2在肝癌發生發展及治療中作用的研究進展[J]. 環境與健康雜志, 2016, 33(2): 178-181.
[19] Saydam O, Shen Y, Würdinger T, et al. Downregulated microRNA-200a inmeningiomas promotes tumor growth by reducing E-cadherin and activating the Wnt/beta-catenin signaling pathway[J]. Mol Cell Biol, 2009, 29(21): 5923-5940.
第5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一般意義上的遺傳學指基于DNA序列改變導致基因表達水平的變化,如基因突變、基因雜合丟失和微星不穩定等,表觀遺傳學指非DNA序列改變,是細胞內除了遺傳信息以外的其它可遺傳物質發生的改變。表觀遺傳學研究主要包括染色體重塑、組蛋白修飾,DNA甲基化,非編碼RNA調控等。
真核細胞的特征是有細胞核,細胞核包含了真核生物幾乎所有的遺傳物質。真核生物基因組DNA儲存在細胞核內的染色質中,核小體( nucleosome) 是構成真核生物染色體的基本結構單位。各核小體串聯而成染色質纖維,核小體DNA長度約為165個堿基對,其中纏結在組蛋白八聚體周圍的核心DNA( core DNA) 約1. 65圈,約合147個堿基對,而相鄰的核小體之間的自由區域( linber DNA) 為20 - 50個堿基的長度,也就是基因組的75% ~ 90% 被核小體所占據。組蛋白八聚體由H2A、H2B、H3和H4各2個拷貝組成,每個核心組蛋白都有兩個結構域: 組蛋白的球形折疊區和氨基末端結構像一條尾巴( tail) 位于核小體的球形結構以外,可同其它調節蛋白和DNA發生相互作用,染色體的高級結構和基因的轉錄調控都與組蛋白密切相關。核小體組蛋白的尾巴可以發揮信號位點的作用。
上面已談到表觀遺傳學是指非DNA序列改變,而是改變染色質結構導致基因表達水平的變化。那么,染色質結構改變如何導致基因轉錄和表達水平改變的呢?
其一,在細胞里,DNA-染色質的形式存在,核小體是染色質的基本結構單位,75% ~ 90% 的基因組存在其中,核心組蛋白的尾巴的各種位點通過多種轉移酶的作用,發生共價修飾,組蛋白通過電荷相互作用( 組蛋白尾巴帶正電荷,DNA帶負電荷) 如組蛋白乙酰化修飾可以通過電荷中和方式削弱組蛋白-DNA或核小體 - 核小體的相互作用,或引起構象的變化,破壞核小體結構,使DNA接近轉導機構,激活轉錄。
其二,為保證染色質的DNA與蛋白質的動態結合,細胞內產生了一系列特定的染色體重塑復合物,也稱重塑子,它們利用水解ATP的能量通過滑動、重建、移除核小體等方式改變組蛋白與DNA結合狀態,使蛋白質易于接近目標DNA。依據重塑子包含的ATP酶中催化亞基結構域的不同,把重塑子分為SWI/SNF、ISWI、CHD、IN080四大家族。組蛋白修飾后如乙酰化的組蛋白可以募集轉錄復合物進入到一個基因位點,影響轉錄。
2 認知過程中的表觀遺傳學機制
通過新信息或經驗獲得的記憶可保持數月、數年,甚至終生,而長時間保持存活的蛋白質或mRNA的半衰期只有24 h,顯然,二者之間存在很大的矛盾,那么記憶的物質基礎到底是什么? 1984年,Crick提出了一個假設,即記憶編碼在染色體的DNA上,雖然當時他并不是十分確信,但現已澄清,染色體是信息的攜帶者,而且可以代代傳下去,染色體結構或化學上的改變與認知功能的關系可作如下的理解: 表觀遺傳學的改變是對來到大腦的信息、應激和神經元活性改變做出結構上的適應,最終將信息帶至并激活特異性基因表達程序。目前研究證明,在腦的一些區域發生的表觀遺傳學改變如組蛋白的乙酰化、甲基化、磷酸化可以穩定地改變動物的行為,包括學習、記憶、抑郁、藥物依賴、突觸可塑性等等,為長記憶的形成、鞏固和突觸可塑性的形成、維持提供解釋[5,6,7,8]。
閱讀近十幾年發表的有關表觀遺傳學文章后,解決了長期以來認知過程中令人費解的一些問題,本文著重介紹在腦的不同區域( 主要是海馬和腦皮層) 組蛋白修飾和DNA甲基化在認知過程中的作用及其可能的機制。
2. 1組蛋白乙酰化[9,10,11]一系列表觀遺傳學改變都能影響記憶過程,其中組蛋白乙酰化,具有明確、顯著地促進記憶的形成和鞏固。組 蛋白乙酰 化是通過 組蛋白乙 酰化酶( HATs) 催化完成的。HATs將帶正電荷的乙酰基轉移到組蛋白N末端尾區內賴氨酸側鏈的-氨基。組蛋白乙酰化酶被分成3個主要家族: GNAT超家族,MYST家族和P300 /CBP家族。將乙酰基從組蛋白移走,由組蛋白去乙酰化酶( HDACs) 催化完成,HDACs被分成4類: Ⅰ類,鋅依賴型HDACs,Ⅱ類和Ⅳ類HDACs,Ⅲ類NAD依賴性HDACs。在哺乳動物中,海馬在記憶形成中起重要作用。許多學者以海馬區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了組蛋白乙酰化對條件性恐懼中的背景記憶( contextual memory) 和空間記憶的影響。研究證明組蛋白乙酰化或抑制HDACs活性都能增強條件性恐懼中的背景記憶和Morris水迷宮中的空間記憶以及增加突觸可塑性( synaptic plasticity) 。應當指出的是,腦中組蛋白乙酰化不是獨立于其它組蛋白修飾而存在,而是在組蛋白乙酰化的同時,也往往存在組蛋白磷酸化、甲基化。組蛋白乙酰化削弱了組蛋白與DNA之間的靜電親和力,從而促進染色體結構接近轉錄基因機構,引起基因持續性改變,增加神經元活動,乙酰化修 飾后的組 蛋白也可 以募集其 它相關因子[10,11,12,13],如轉錄復合物,進入到基因位點,影響轉錄。
2. 2 組蛋白乙酰化的調節機制[14,15,16]
2. 2. 1神經元活性與組蛋白乙酰化組蛋白乙酰化可由許多類型的神經元活性所調節,例如,KCl介導的神經元去極化引起海馬培養中的核心組蛋白H2B乙酰化的增加,再如,特異性受體激動劑可興奮多巴胺能、乙酰膽堿能、谷氨酸能途徑,增加小鼠海馬H3K14和H3S10的乙酰化,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組蛋白乙酰化都伴有細胞外調節激酶ERK( MAPK家族中的一員) 的激活,直接激活MAPK-ERK信號途徑可增加組蛋白乙酰化,而MAPK-ERK抑制劑則可阻斷組蛋白乙酰化[16,17,18],這些研究表明,神經元活性引起組蛋白乙酰化是通過MAPK依賴性途徑的激活,而且也可能是通過H3S10磷酸化之間的對話。后者常與在蛋白乙酰化同時存在,從染色體脫離的HPAC2引起的神經活性,也能改變組蛋白的乙酰化,用BDNF刺激皮層神經元,能引起HDAC2在胞嘧啶262和274位的硝基化及隨后組蛋白的高乙酰化及隨后組蛋白的乙酰化,并伴有神經營養因子依賴性基因表達的增強。已知MECP2可增加BDNF的表達,但被HDAC2負面調節。因此,神經活性參與了以HDAC2和BDNF為中心的正性反饋,該系統導致組蛋白乙酰化和基因自身的持續表達。
2. 2. 2突觸可塑性與組蛋白乙酰化長時程突觸可塑性涉及突觸維持和交流有關基因表達的改變,已有充分材料證明,組蛋白乙酰化促進這一改變,例如在海兔( Aplysia) 組蛋白乙酰化能誘導長期易化 ( LTF) 并伴有CREB結合蛋白CBP的增加[19],類似的改變也在突觸素( synapsin) 的啟動子區域觀察到,突觸素與LTF和LTD均有關。不過,伴有CREB乙酰化的減少,正常情況下,誘導LTF需施加強電刺激,但如果提前給予RNA干擾( RNAi) ,弱的電刺激也能誘導LTF。這一發現提示,組蛋白乙酰化程度與突觸可塑性程度密切相關,HDAC1能增加天然存在的突觸傳遞過程,在哺乳動物的LTP也與組蛋白乙酰化水平有關。LTP誘導可平行出現H3和H4組蛋白乙酰化的增加,從研究中還明顯看出LTP促進乙酰化,改變特異地存在于與突觸傳遞有關基因如Reelin和BDNF啟動子區域,這一結果與前述看法一致,即在組蛋白乙酰化過程中存在一個基因自身持續性改變的正性反饋系統。此外,有關HATCBP的研究表明,增加組蛋白乙酰化能促進LTP,部分或完全缺失CBP功能的小鼠出現組蛋白乙酰化水平的下降和LTP形成受阻。不過,不依賴轉錄的早期LTP不受影響。
2. 2. 3記憶形成與組蛋白乙酰化[20,21]在低等生物和哺乳動物進行的研究證明,不管哪種記憶類型或哪種記憶時相( 記憶獲得,鞏固和再現) 都能對組蛋白乙酰化進行調節,例如背景性和線索性恐懼記憶( fear memory contextual and fearmemory cued) 都能增加H3乙酰化,小鼠眨眼條件反射( eyeblink conditioning) 和大鼠潛伏抑制 ( latent inhibition) 能分別增加組蛋白H3和H4乙酰化,大小鼠物體識別記憶( Objectrecognition memory) 伴有H3和H4乙酰化的增加,此外優先食物轉換( social transmission of food preference) 和食物厭惡記憶( food aversion memory) 等均能增加H3乙酰化,空間記憶( spatial memory) 伴有H2B,H3和H4乙酰化。
從上述組蛋白乙酰化研究的論述可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 1) 組蛋白乙酰化,不是脫離開其它組蛋白修飾而獨立存在,即在發生組蛋白乙酰化的同時,也有組蛋白磷酸化、甲基化等的發生,其它表觀遺傳學改變對組蛋白乙酰化起了協同作用。
( 2) 神經元活性可調節組蛋白乙酰化,神經元活性的啟動需要MAPK-ERK信號途徑的激活。
長記憶和突觸長時程增強均涉及許多基因的轉導和表達,最常見和最重要的基因包括即早基因Zif/268,Creb,Bdnf和Reelin等。
( 3) 許多種類的神經活性存在一個以BDNF和HDAC2為中心的正性反饋系統,該系統可導致組蛋白乙酰化和基因自身持續表達程序。
( 4) 在多種生物體和細胞研究中觀察到各種不同類型的記憶模式和不同記憶時相都能引起組蛋白乙酰化,進而促進記憶和有關基因的轉錄和表達。
( 5) 組蛋白乙酰化能引起長記憶的形成和鞏固,但對無須轉錄的短記憶和早期LTP沒有影響。
2. 3神經元活性是如何引起組蛋白乙酰化,它的作用機制是什么?[11]途徑之一,神經元活性包括LTP和學習激活G蛋白偶聯受體( GPCRs) ,然后依次激活腺苷環化酶( AC) 產生c AMP,后者激活PKA,PKA磷酸化MEK( MAPK家族中的一員) ,MAPK的家族成員能直接磷酸化組蛋白,隨后啟動組蛋白乙酰化。
途徑之二,神經元活性可通過鈣內流引起膜去極化,然后激活CAMKⅡ,后者磷酸 化甲基-CPG結合蛋白2( MECP2) ,使MECP2從染色體脫離出來,Calmodulin刺激BDNF啟動子區域的基因轉導。BDNF激活一氧化氮合酶導致組蛋白乙酰化酶2( HDAC2) 的硝基化,在硝基化作用下,HDAC2從染色體中脫離出來并強化硝基化,結果引起BDNF表達并參與正性反饋系統,進而促進記憶 - 持續性基因表達的改變( 見Fig 1) 。
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工作指出: 激動NMDA受體,抑制磷酸二酯酶( PDE) ,增加細胞內鈣等多種途徑均可激活PKA,PKA則可直接激活CBP,如前所述。含有乙酰轉移酶活性的CBP與CREB結合,是提高突觸可塑性形成長記憶的必備條件; NO啟動組蛋白影響記憶的機制有二,一是激活N0-cG MP-Ca MKII-CREB磷酸化的信號轉導途徑; 二是NO依賴性的HDAC的5-硝基化,可增加組蛋白乙酰化,而NO供體與5-硝基谷胱甘肽,可抑制HDAC活性,因而,也能增加組蛋白乙酰化。此外,神經元活動或突觸活動引起胞外鈣內流入神經細胞內,使Me CP2的S421磷酸化,S80去磷酸化,后者從染色質分離出來,發揮對神經可塑性和記憶的調控作用。
2. 4 RNA干擾 ( RNA interference,RNAi)指內源性或外源性雙鏈RNA( dsRAN) 介導細胞內mRNA發生特異性降解,導致靶基因表達沉默,產生相應功能表型缺失,RNA干擾下的基因沉默是表觀遺傳學的重要內容,人工合成的小RNA( SiRNA) 包括miRNA和SiRNA。小RNA序列較短,能指導Argonaute蛋白識別的靶分子并導致基因沉默。
已證明,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阻遏學習記憶,并在細胞內有廣泛分布,人工合成HDACi顯然有重要的治療價值,HDAC2的結構很接近HPAC1,盡管如此,科學家們還是合成許多類型的HDACi,上述各種類型學習記憶和突觸可塑性模型證明使用HDAC2i可促進記憶,增強LTP,阻遏記憶下降。
3 組蛋白和 DNA 甲基化[20,21]
甲基化可發生在組蛋白,也可發生DNA上。盡管這二種甲基化產生的方式、調節機制和涉及的酶與蛋白等有所區別,但二者甲基化的結果是一致的,即他們都能激活基因的轉錄與表達,從而促進長記憶的形成和提高突觸可塑性。這點學術界的看法一致,沒有任何異議。下面將重點介紹組蛋白和DNA甲基化是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基因轉錄及長記憶和突觸可塑性的?
真核細胞中,甲基化只發生在胞嘧啶第五位碳原子上,是由甲基轉移酶所催化,以S-腺苷甲硫氨酸( S-adnosylmethionine,SAM) 作為甲基供體,將甲基轉移到胞嘧啶上,DNA甲基化主要發生在Cp G雙核苷酸序列的胞嘧啶上,哺乳動物異染色質的DNA約有80% 的CPG被甲基化,根據作用方式和反應酶不同,DNA甲基化分為兩種: 維持甲基化( maintenance methylation) 和從頭甲基化 ( de novo methylation) ,前者與DNA復制相關聯。當甲基化的雙鏈DNA被復制生成兩條的新的雙鏈DNA后,只有親代鏈是甲基化的,甲基轉移酶是DNMT1,后者則是DNA上甲基化狀態的重新構建,它不依據DNA復制在完全非甲基化的DNA堿基位點上引入甲基,是甲基化的建立機制。甲基轉移酶依賴于DNMT3a和DNMT3b的活性。
對基因轉錄的影響: 目前研究發現,組蛋白精氨酸甲基化常伴隨轉錄的激活,賴氨酸殘基上的甲基化則因賴氨酸所在的位置不同而有差別,賴氨酸甲基化發生在組蛋白H3的第4,第9,第27,第36,第79( K4,K9,K27,K36,K79) 位及H4K20位上,其中,在酵母和哺乳動物細胞中H3K4和H336位點被甲基化可以激活轉錄,而H3K9 K27 K79和H420的賴氨酸甲基化則可抑制轉錄。
DNA甲基化對基因表達的調節主要表現為抑制轉錄活性,一種可能的機制是由于DNA甲基化直接抑制了轉錄因子的結合,不能形成轉錄復合體,從而也就抑制了基因轉錄活性[16,18,20]。
對記憶的調節作用: Swati Gupta及其同事[21]研究了組蛋白甲基化對成年動物海馬部位記憶形成的影響,他們的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結果: 恐懼記憶能觸發海馬CA1區H3K4三甲基化( 轉錄激活標志) 和H3K9二甲基化( 轉錄抑制標志)的變化; H3K4特異的甲基化轉移酶MⅡ缺失的小鼠出現長記憶形成障礙; 改變組蛋白甲基化與去乙酰化酶( HDAC) 抑制相偶聯; H3K4三甲基化明顯增加兩種基因 ( Zif/268和Bdnf) 的啟動子,這一事件出現在記憶鞏固期間,已知這兩種基因在記憶形成和神經可塑性中起重要作用。這些發現支持組蛋白甲基化在長記憶鞏固中扮演重要作用,其他許多學者也都證明DNA甲基化與記憶形成和儲存有關,如甲基化CpG結合蛋白1( methyl-Cp G-binding protein1) 基因缺失出現空間記憶能力喪失,甲基化CpG結合蛋白2 ( methyl-Cp Gbinding protein 2) 基因缺失的突變小鼠出現恐懼記憶、空間記憶和物體識別記憶的障礙。
海馬DNA甲基化,對記憶形成起重要作用,但海馬的改變是短暫的,訓練后1 d之內便恢復到基礎水平,長記憶以及記憶的鞏固和儲存依賴于腦的不同區域,據信長記憶的形成和鞏固主要依賴于背側前額葉前扣帶皮層( dm DFC) ,為此探討皮層組蛋白甲基化是否能促進長記憶的形成和鞏固十分必要。Miller等采用背景性恐懼記憶試驗探查皮層DNA甲基化對長記憶的影響,報道認為大鼠恐懼條件化環境中的背景記憶可維持數月,在這期間,近期( recent) 記憶會轉變成遠期( remote) 記憶,也即記憶從海馬( HPC) 轉變成依賴于dmP FC的記憶。首先,采用Me DIP即甲基化DNA免疫沉淀法測定皮層三種基因Zif/268,reln和Ca N的甲基化水平。動物試驗則觀察訓練后7 d的背景記憶,將動物分為背景組( C) 、休克組( S) 和背景加休克組( CS) 。結果表明,在所有組和所有測定時間點,即早基因Zif/268均為去甲基化,說明環境刺激能廣泛地改變dm PFC Zif/268的甲基化狀態,相反的,一個記憶正性調節基因Reln僅在受訓練的動物即CS組動物訓練后1 h內出現高甲基化,隨后即回歸對照水平,訓練后短時間內Ca N( 一種記憶抑制基因) 的甲基化無改變,但在訓練后1 d,這一基因出現持久的甲基化,隨后用BSP描繪訓練后7 d Ca B甲基化的改變,發現僅CS組動物有顯著的Ca N甲基化。為了解皮層DNA甲基化是否能反映聯合學習,動物在訓練前注射NMDA受體拮抗劑MK-801,證明MK-801干擾了訓練后7 d動物恐懼記憶的獲得( acquisition) ,也阻斷了訓練后2 d dmP FC Ca N和Reln的高甲基化,但不影響Zif/268的甲基化,進一步支持Ca N和Reln高甲基化是一種對聯合性環境信號的特異性反應。Frankland等前期研究觀察了訓練后不同時間對ACC( anterior cingulate) 恐懼記憶再現( retrieval) 的干擾。結果證明ACC在18 ~ 36 d( 近期記憶) 經干擾失去記憶再現,但不是訓練后1 d或3 d( 近期記憶) ,從這一結果估計記憶的鞏固出現在訓練后3 ~18 d,研究還證明皮層DNA甲基化可能在訓練后1周內出現,該時段也是皮層留下記憶痕跡的時間,隨后的實驗證明訓練后立即向背側HPC( CA1) 注射NMDA受體選擇性抑制劑AVP,證明APV不但能干擾學習,也能阻止訓練后7 ddmP FC Ca N和Reln甲基化,表明一次性海馬 - 依賴性學習經驗就足以驅動皮層長時間、基因特異性甲基化改變,為了進一步探討皮層DNA甲基化是否伴隨長記憶的形成,觀察了訓練后30 d的皮層甲基化及記憶鞏固的情況,結果證明在CS動物皮層的Ca N甲基化仍十分明顯,而且與長記憶的出現和維持的時間段相吻合,此外還觀察到在HPC有快速甲基化,而在dm PFC有持久的甲基化,以上研究闡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海馬HPC可啟動學習記憶,產出過渡性短記憶,第二,長記憶的形成和鞏固依賴于dm PFC,第三,海馬和皮層記憶的形成均緣于海馬和皮層DNA的甲基化,或甲基化與其它組蛋白修飾的協同作用,第四,重要的記憶相關基因和受體包括Zif/268,Reln,Bdnf和NMDA受體。組蛋白甲基化是如何調整認知過程,它的生物學機制是什么?Day和Sweatt提出了闡明組蛋白甲基化是表觀遺傳學標志的假說[20],如在細胞內轉變成功能性后果,出現三種可能性: 第一、DNA甲基化驅使神經細胞的反應狀態發生了改變,即它允許、容納其它機制參與進來產生協同效應和維持更加長遠的改變; 第二、甲基化事件積極參與和改變基因的讀出,促進記憶的進行,例如增加突觸強度和突觸可塑性; 第三、表觀遺傳學機制幫助神經細胞無增殖( aplastic) ,在神經元無增殖的情況下可以以穩定突觸數量( synaptic weight) 的分布,后者是穩定記憶的必需條件,這一假設強調了突觸可塑性在記憶過程中的重要性,事實上,國際上近年的研究表明老年癡呆認知功能的衰減與老年斑、A腦內沉積及神經纖維纏結無明顯相關,由于突觸在信息傳遞、信息加工中的重要作用,許多學者都支持突觸功能降低( 包括突觸效能下降和突觸丟失) 是造成認知功能障礙乃至老年癡呆的主要原因,當前治療老年癡呆和各種認知障礙的治療方向都在尋找加強突觸效能,防止突觸丟失、增加突觸新生的新藥。
3. 1組蛋白磷酸化[25,26,27]組蛋白磷酸化修飾跟乙酰化和甲基化修飾一樣具有調節認知功能的作用,這一修飾發生在組蛋白的H3、S1和S10絲氨酸殘基上,由一組蛋白激酶包括絲裂原和應激激酶( MSKI) 和Aurora激酶家族催化完成。組蛋白磷酸化可被蛋白磷酸酶PP1和PP2a所逆轉,這兩種脫磷酸化酶又可被其它分子級聯包括多巴胺和c AMP調節的磷酸蛋白32( DARPP32) 所抑制。最具特色的磷酸化標志存在于H3第10位( H3K10) 絲氨酸上,這一修飾招募了含有HAT活性的GCN5,因而能增加鄰近組蛋白賴氨酸殘基K9和K14的乙酰化,這解釋了為什么組蛋白乙酰化和磷酸化常常同時存在。另外,H3S10磷酸化通過改變DNA和組蛋白尾部間的交互作用增加轉錄因子的結合。
許多研究工作已揭示組蛋白的磷酸化具有調節記憶形成的作用,編碼RSK2的基因突變能產生低咖啡攝入綜合癥( coffin-lowry) ,有精神遲緩、精神異常等表現。在動物模型上的研究,背景性恐懼條件反射形成后,H3S10磷酸化和H3S10 / K14磷酸乙酰化迅速增加,但ERK抑制后可阻斷其增加。同樣的,缺失MSKI的小鼠出現恐懼記憶和空間記憶障礙,這一缺陷卻不因給予HDAC抑制劑所逆轉,提示組蛋白磷酸化途徑與組蛋白乙酰化并行而不是位于乙酰化的下游,與此相協調的是,組蛋白磷酸化酶PPI受抑制,能改善長時程物體識別記憶和空間記憶而不影響短記憶,從這些發現推測: 通過抑制PPI來增加組蛋白磷酸化對治療學習記憶障礙可能是一個有明顯特色甚至是互補的治療策略。
除學習記憶外,H3S10磷酸化也與藥物成癮行為學反應有關聯。可卡因可引起紋狀體H3S10磷酸化的增加,敲除MSKI的小鼠出現對服用可卡因行為反應的障礙。核內積累的DARPP-32能影響對可卡因和蔗糖獎勵的行為反應。組蛋白磷酸化也已被證實是抗精神病和抗巴金森氏癥下游的一個重要靶標,針對表觀遺傳學這一組蛋白磷酸化修飾設計和開發有治療潛能的化合物是很有意義的。一項有意義的研究指出,MSKI主要存在于神經元和紋狀體、杏仁核、海馬等腦區,MSKI這一選擇性分布是治療干擾藥物成癮的一個很好的候選者。
哺乳動物細胞Aurora激酶家族成員的結構和功能在進化上保守,根據該家族成員在細胞內的定位可分為3種: Aurora-A,Aurora-B和Aurora-C。Aurora-B是有絲分裂中組蛋白H3的第四位絲氨酸磷酸化所必需的激酶。組蛋白H3磷酸化主要由Aurora-B激酶控制,除MSK和Aurora外,IB激酶( nuclear,IKK) 復合物中的異構體( IKK) 也可以調控海馬區域組蛋白的磷酸化修飾,IKK是核因子B的一種去抑制調控子,抑制IKK可以阻止背景性環境下長期記憶的再鞏固( reconsolidation)[24]。
組蛋白磷酸化促進長記憶形成和鞏固的機制主要是磷酸基因攜帶的負電荷中和了組蛋白上的正電荷,造成組蛋白與DNA親和力的下降,使DNA容易接近轉錄機構,激活基因轉錄,這是長記憶形成所必需的,也解釋了為什么組蛋白磷酸化不影響短記憶。
在正常生理和表觀遺傳學的生化反應中,磷酸化使蛋白質和基因活化,隨后的生化和生物學反應才能繼續進行,所以在細胞繁殖、分化、細胞存活、DNA復制、轉導和重組、細胞凋亡以及信號轉導中發揮重要作用。
3. 2 其它組蛋白修飾與認知功能[27,28,29]
組蛋白泛素修飾涉及三類催化酶: 泛素激活酶( ubiquitin activating enzyme,E1 ) ,泛素接合酶 ( ubiquitin conjugatingenzyme,E2) 和泛素連接酶 ( ubiquitin protein ligase,E3 ) 。依賴這三種酶分三步進行泛素化修飾,第一步E1利用ATP形式存在的能量與泛素結合成高能硫酯鍵,構成泛素 - E1偶聯物將泛素激活; 第二步,通過轉酯作用將活化的泛素轉移到泛素結合酶E2的活性半胱氨酸殘基上; 隨后,E2將活化的泛素轉移至泛素連接酶E3上,形成高能量E3 - 泛素偶聯物,最后E3可直接或間接地促使泛素轉移到特異靶蛋白上,使泛素的羧基末端與靶蛋白的賴氨酸的-氨基形成肽鏈或轉移到已與靶蛋白相連的泛素形成多聚泛素鏈,有一個去泛素酶大家族,從賴氨酸殘基上移去泛素。
組蛋白泛素化有廣泛的細胞功能,最著名的是控制轉錄的啟動和延長,泛素酶/去泛素酶與其它組蛋白修飾,特別是與組蛋白甲基化有牽連,組蛋白泛素化與神經退性病變之間的關聯來自亨廷氏病,Huntington與泛素連接酶h PRC12存在交互作用。在多個亨廷氏病動物模型上觀察到泛素化的H2A的增加和泛素化的H2B減少,導致組蛋白甲基化模式的改變和基因轉錄下調,故以泛素連接酶為靶標設計藥物對亨廷氏病可能有潛在的治療價值。
多聚( ADP-核糖) 聚合酶[poly( ADP ribose) polymerases,PARPS]在與記憶行為有關的組蛋白修飾中起一定作用,PARPs可催化ADP核糖單位從NAD+轉移到組蛋白靶位點上,不僅可影響染色質的局部結構,還可影響轉錄因子及染色質重塑復合體的結合,在操作性條件反射和位置回避實驗中均證明PARP1可增加長記憶的形成。
3. 3衰老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的表觀遺傳學[27,28,29,30]衰老和年齡相關性神經退行性疾病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過去有大量報道衰老與神經退行性疾病沒有太多差異,如老年癡呆出現各種病理改變也在衰老過程中出現,但從未從表觀遺傳學方面去尋找原因,現有的研究揭示,表觀遺傳學的異常修飾是衰老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的主要機制,其主要病理特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組蛋白和基因組DNA甲基化的減少,在衰老和神經退化性疾病中表現突出,如神經細胞和基因組DNA亞甲基化( hypomethylation) 和甲基轉移酶( HAT) 活性缺失,在AD患者的病理性神經元和基因組DNA的亞甲基化水平更低。Mastroeni等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了死后AD和非AD( ND) 病人眶內皮層Ⅱ神經元的DNA甲基化和8種甲基化維持因子的免疫反應性,發現ND和AD神經細胞核具有甲基化胞嘧啶免疫反應陽性的神經細胞數分別為91. 7% 1. 3% 和39. 9% 3. 4% ,甲基化胞苷呈陽性的細胞數分別為91. 1% 1. 3% 和51. 8% 6. 1% ,即AD病人的兩種甲基化模式比ND病人明顯降低,DNMT,MOD2和P662均系甲基化維持因子,在ND病人神經元呈免疫反應陽性,而AD病人神經元免疫呈陰性,此外,RPL26和5. 8 SrRNA也有量的減少。
其二,HDAC2表達增加,研究證明神經退行性改變、衰老和長期應激都能引起HDAC2表達增加,如在神經退行性疾病和衰老時,神經毒性因子如A,氧化應激( H2O2) 和細胞內D25和CDK5激活,糖皮質激素受體( GR) 與臨近組蛋白HDAC2啟動子區的GR反應元件( CRE) 結合,增加腦內HDAC2水平,HDAC2優先與學習、記憶、神經可塑性有關的基因如BDNF結合,同時降低組蛋白乙酰化和基因的表達,破壞BDNF介導的正性反饋系統,從而降低神經可塑性和記憶的形成與鞏固。
第6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兩篇研究揭示嚙齒類動物的中含有一定數量的RNA,這些RNA分子能夠影響子代的代謝活動。由于這些RNA是幫助合成蛋白質的關鍵元件(即轉運RNA),因此這一發現揭示了一類新型的遺傳物質。來自西雅圖西北太平洋糖尿病研究所的遺傳學家約瑟夫?納多認為這一發現十分的令人震驚,但也不是完全毫無可能。
這一項研究揭示了一類新的RNA分子――轉運RNA。其中一項工作中,遺傳學家奧利弗? 蘭度向雄鼠飼喂低蛋白的飼料,發現這些雄鼠細胞中參與膽固醇與脂肪代謝的基因表達水平上升。之后,他們分析了這些雄鼠中的成分,發現其中含有相當數量的轉運RNA,并且證明了這些轉運RNA是在經過附睪過程中積累的。
另外一項研究則是由中科院的一個研究組做出的。他們通過向雄鼠飼喂高脂或低脂的食物,之后將這些雄鼠的注入未受精的卵子中。之后,他們開始追蹤后代的代謝活動的規律(這些后代小鼠均飼喂正常食物)。結果顯示,飼喂高脂食物的雄鼠的后代雖然體型較瘦,但還是顯現出了肥胖與糖尿病的相關癥狀:葡萄糖攝入異常,胰島素耐受。為了證明是否轉運RNA參與其中,研究者將這些轉運RNA單獨注入未受精卵子中并讓其接受正常的受精。結果顯示,即使單獨注入接受高脂食物的雄鼠中的轉運RNA,也會使后代產生代謝異常的癥狀。
如今,研究者需要回答“這些遺傳性狀是否穩定,能否通過改變飲食的方式矯正”。RN段的作用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如果壞的飲食習慣能夠遺傳給下一代的話,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好的飲食習慣也能遺傳下去。 父親可能影響孩子腦發育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國際學術期刊PNAS上發表了一項研究進展,他們在分子水平上發現了應激如何改變雄性小鼠的,并通過這種方式影響其后代對應激的應答情況。他們還發現這種變化是通過表觀遺傳學的方式或microRNA進行傳遞的,并非通過改變DNA。
在早期研究中,研究人員已經證實在之前通過更換籠盒或進行狐貍尿(捕獵者氣味)暴露處理雄性小鼠,使其處于應激狀態,其后代對應激的應答情況會存在障礙。研究人員將受到應激的雄性小鼠和未受到應激的雄性小鼠的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在應激小鼠中有9種microRNA表達出現升高。
為進一步證實這一結果,研究人員將這9種microRNA通過顯微注射的方式注入小鼠受精卵,隨后植入正常雌性小鼠體內進行繁殖,并以假注射或注射單個microRNA作為對照。當子代小鼠成年后,研究人員檢測了這些小鼠對應激的應答情況。研究人員表示,檢測結果與他們之前觀察到的結果完全匹配。
當接受多microRNA注射的小鼠受到輕微應激,它們體內可的松水平更低,這表明這些小鼠在早期神經發育過程中存在非常廣泛的變化。
研究人員對這幾個microRNA的靶向mRNA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來自母親卵細胞的mRNA受到了microRNA的攻擊,并導致這些受到攻擊的mRNA水平發生下降,研究人員還特別指出,這些受到影響的mRNA主要編碼參與染色質重塑的蛋白分子。
研究人員表示,他們接下來準備對導致microRNA釋放的上游因子進行進一步研究以及是否能夠通過給予獎勵等方式對上述過程進行干預,防止雄性親代將異常應激反應傳遞給下一代。 母親遺傳給女兒負責情緒調節的腦結構
第7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研究生;創新;分子生物學;教學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02-0070-02
隨著知識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展,高等學校以傳承知識為主的傳統教育模式正向強調能力與素質培養的創新教育模式轉變。如今,創新已成為一種時代精神,培養高素質的創新人才是時代對高等學校提出的迫切要求。但由于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教育規模的擴大,使得研究生教育階段的人才培養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一刀切”的現象,制約著創新型研究生人才的培養。因此,加強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凸顯其空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目前我國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著學生自主探索學習能力不足,研究創新能力較低,而導致這些問題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現在的教學體系對研究生的創新學習能力培養不夠[1]。在發達國家的研究生教育課程中,講座式、研討班式和案例式的課程比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高達40%~50%。與國際著名大學相比,我國的研究生教育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還存在一定差距,表現在以傳統的理論課教學為主,進行灌輸式教學,大大限制了學生的自主性和創新性。
分子生物學自誕生以來,是生命科學發展最為迅速的前沿學科,已滲透到生命科學的各個領域。《分子生物學》一直是本校基礎與臨床各醫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必修課程,但由于其內容偏抽象難以理解、知識更新又快,傳統的教學方法使得學生的學習效果并不理想。新時期分子生物學的教學目標不再是單純讓學生掌握基本的分子生物學原理,更要讓學生學會如何應用這些基礎知識來解決當下所面臨的醫藥科研難題。鑒于此,筆者嘗試對我校2014級醫學類研究生的分子生物學課程進行改革,在傳統的傳授式教學基礎上注重多種啟發式教學方式的應用,以未采取教學改革的2013級研究生為參照,評估教改前后教學效果,以探討新型教學模式對研究生自主性學習及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影響。
一、分子生物學課堂教學中多種教學方式的實施
1.教材與最新研究進展的結合。在講授分子生物學理論知識的同時,筆者注重介紹最新的國際學術動態和科研成果,引導學生去探索新的知識,培養其創新思維。例如在講到真核基因表達調控的染色體結構與真核基因表達密切相關時,我們會給大家提及現在比較熱門的“表觀遺傳學”。給學生們介紹些影響因子比較高的表觀遺傳學方面的英文文章,布置他們閱讀文獻后寫出相關綜述。使大家認識到表觀遺傳對基因表達的調控不僅體現在DNA的甲基化,組蛋白的乙酰化、甲基化以及一些非編碼校RNA的調控都屬于其調控范疇。這樣,同學們不僅掌握了表觀遺傳的概念,對其技術路線和應用等方面都有所涉獵;一定程度上又提高了他們閱讀英文文獻的能力,對他們以后進入課題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2.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方法的應用。PBL是一種強調以學生主動學習為主,提倡以問題為基礎的討論式、啟發式教學方法[2]。它是由1969年美國的神經病學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創立,目前被國際公認的培養創新型人才的一種教學方式。
PBL的教學組織形式是“教師提出問題―個人查找資料準備―集體研討”。首先教師要提出具有探索性的問題,一方面要兼顧教學的重點內容,另一方面要結合國內外研究熱點。比如在講到分子生物學的基因組學、轉錄組學和蛋白質組學等各種組學研究時,我們針對醫學類研究生提出的問題是“試述主要組學有哪些,組學如何推動未來醫學的發展”。同學們分組進行準備和討論,考慮到學時有限,2014級選修學生數達358人,我們采取的是8~10人一組,每個小組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討論,自行選定題目,小組人員分工合作查閱各類文獻資料,認真地分析討論,最終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案,并以PPT形式在課上進行總結匯報。根據匯報內容的完整性、條理性、創新性等由老師及其他組人員分別進行打分。該種教學模式引發了同學們對分子生物學學習的興趣,不僅培養同學們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還增強了團隊協作能力。
3.專題講座式教學方式的應用。在分子生物學課程內容安排中,我們還嘗試邀請校內科研工作者進行了“如何進行科研論文的寫作”和“如何撰寫基金申請書”兩次實用的科學研究方法專題講座。例如我們邀請本校獲得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擁有“河北省優秀科技工作者”殊榮的教師給學生們講解國家、省自然科學基金的寫法及體會。進行講座的老師從項目題目的寫法開始,到立題依據、研究內容與目標、研究方案、可行性分析、項目特色與創新、經費預算及工作基礎和條件,不僅向同學們展示了基金書寫的全部流程,還介紹了自己的一些寶貴經驗。通過這次講座,不僅對同學們馬上要進入的選題階段有很大益處,從長遠來看對他們以后獨立進行課題申請也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二、教改實施后的效果評價
目前,我校研究生的分子生物學課程考核還是以試卷考核為主,試卷考核作為期末成績占總成績的70%,平時成績占30%。試卷70%的內容以教材的基礎知識為主,30%為課堂相關內容的拓展和深入。平時成績由上課出勤情況和平時作業組成,作業由教師布置與教學內容相關的問題和綜述組成。為了評估應用多種教學方法的教學效果,我們對實施教改的本校2014級358名醫學專業研究生與以單一式講授式教學方式為主的2013級362名研究生的分子生物學平均成績進行分析比較。結果如表1所示,2014級研究生無論是平時成績、期末成績還是最后總成績均高于2013級研究生,其中總成績之間比較具有顯著性差異(P
以上比較結果顯示,教改后的2014級研究生的分子生物學成績普遍高于2013級學生。平時成績高不是出勤率變化有多大,主要源于2014級學生平日作業成績提高,考慮可能是老師設定問題后,同學們以小組形式查找文獻資料再討論、總結,比原來自己單獨查資料更有效,從而獲取的信息更豐富、材料組織得更加全面和深刻。期末成績比原來高,其實基礎理論成績變化不大,主要是拓展內容部分成績提高了。筆者考慮這與采用新型教學模式使同學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并思考最新的科研進展是密不可分的。
三、結語
研究生課程教學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系統工程,其質量高低直接影響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以往的研究生課堂教學以傳授性方式為主,老師作為中心,學生是被動的聽眾,培養的人才大多缺乏想象力和創新能力,與21世紀國際競爭對創新人才的需求背道而馳[3]。本文筆者以醫學專業研究生為研究對象,對分子生物學課程進行改革,教學方式由原來單純的講授式教學向綜合應用各種教學方式轉變。將PBL和專題講座等啟發性教學方式滲透進傳統教學模式中,努力實現以學生為中心,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只是組織、指導和促進者的轉變。在理論教學中注重增加學術前沿內容,開拓學生視野,培養學生科研興趣和創新思維。教改的調查結果顯示新型教學模式獲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不僅幫助了學生更好地掌握理論知識從而提高考試成績,最重要的是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主動性,學會科學研究方法、培養科學創新能力,這對于培養新時期同時從事教學、科研、醫療的高級醫學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彬,楊克虎,田金徽,等.改革培養模式,造就創新人才――研究生循證醫學教學改革實踐[J].中國循證醫學雜志,2009,9(4):481-483.
第8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分子生物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創新生物學人才
分子生物學的目標是在分子水平上闡明細胞活動的規律,從而揭示生命的本質[1]。雖然它在生物類專業課程體系中充當著重要角色,對生命科學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分子生物學的教學卻因為課程內容多,學科交叉廣,理解難度高,信息量大,知識更新快而使教學效果差強人意,集中表現為教師授課難和學生學習難。這種現狀不但困擾著老師和同學,也與大學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目標不相適應。如何克服分子生物學課堂教學的“瓶頸”?本人在從事十多年的分子生物學教學過程中,努力研究和探索多種形式的教學改革,力求提升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
一、教學內容的合理組織
分子生物學的教學除了選用好的教材,制定完善的教學大綱,如何組織教學內容是教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環節[2]。教學內容呈現給學生的應該是完整、清晰的、有層次、條理的知識。我們在組織教學的過程中,首先從提高自身學科素養著手。“一本教材書,數種參考書”,除分子生物學國內、國外各類版本外,與分子生物學相互交叉和滲透的其他學科,如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遺傳學,我們也都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和強化,不斷夯實專業知識、拓展專業領域,基本構建了分子生物學完整的知識體系,具備了對教材處理的前提。既避免了教學中各學科的重復,也進一步凝練了知識。此外,我們還通過網絡教學平臺向全國優秀教師學習,在不斷的探索中總結出了教學內容合理組織的一些思路。1.思維導學模式。在DNA復制教學環節,知識點多,并且較分散,很容易在教學中造成學習困難和知識混淆的現象,針對這章教學的特點,我們采用了思維導學模式,收到了非常好的教學效果。2.重點、難點解讀。本科教學形式多樣化,也更提倡學生的自主學習,但并不是淡化了教師的教學,反而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教師必須圍繞每堂課的教學目的,合理組織和引導學生理解并掌握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內容。比如在講解染色體端粒末端修復機制中,教師首先要從教材的知識結構中梳理出重點。染色體端粒末端修復機制的知識點包括:(1)引物切除造成的遺傳信息缺失;(2)端粒末端的特點;(3)體細胞和性細胞末端修復機制的不同;(4)DNA結構的變化;(5)端粒酶的修復機制。梳理知識點后,總結教學重點:一是引物切除后損傷修復在體細胞和性細胞中的不同;二是四鏈DNA結構;三是端粒酶的修復機制。其中端粒酶修復機制的講授是學生學習的難點。難點集中在端粒酶的性質和修復發生的過程。經過對教學內容中重點和難點的準確把握和合理組織,教師才能在課堂教學中突出重點、突破難點,讓學生的課堂學習無障礙。
二、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進
教學方法的推陳出新,是教學改革的重要內容[4]。為發揮學生作為教學主體的能動性,我們根據具體的教學內容設置了啟發式、聯想式、探究式等多種教學方法[5],讓學生參與到教學過程中,不僅活躍了課堂氣氛,而且在分享知識的同時,更注重教會學生靈活掌握學習的方法。
1.啟發式教學。啟發的目的在于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針對每一次的課堂教學,設計一些拋磚引玉的問題,供學生思考與討論,這成為了分子生物學理論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進行到真核生物基因表達調控學習環節,提出甲基化修飾的生物學意義,這個問題覆蓋范圍廣,涉及到了DNA復制的調節、蛋白質和DNA甲基化修飾對基因表達的調控,以及Epigenetic(表觀遺傳學)方面的知識。通過提出問題—討論分析—不斷啟發—再討論分析—歸納總結—解決問題這一系列的互動教學活動,充分調動了學生課堂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不斷的討論分析中通過展示不同的思維、發表各自的觀點,不但有利于促進學生在學習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且有利于學生通過對基礎知識的消化、理解來達到理論的升華、拓展[4]。
2.聯想式教學。分子生物學是在生物化學、細胞生物學和遺傳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6],因此知識相互交叉、相互滲透。在授課的過程中,教師一方面要避免重復,一方面要通過聯想知識點適時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提高學生對知識的遷移能力和整合能力。如在講解化學修飾對基因的表達調控時,將細胞生物學中的信號轉導有機結合,使學生了解基因表達調控對細胞信號轉導的作用機制。
3.探究式教學。在分子生物學教學中,每一個理論知識的背后都是科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如確定遺傳物質是DNA的兩大經典實驗,我們以探究的形式呈現教學內容,從實驗設計,到結果顯示,再經過討論分析并得出結論,以課題研究的角度,研究人員的身份引導學生進入學習角色,將學科概念、理論產生的起因和過程展示給學生,啟發學生努力探索,走近科學,讓學生從中領悟知識形成的探究性和科學性,逐漸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能力的高素質研究型人才。4.多媒體多樣化教學。分子生物學的教學內容具有微觀性、復雜性、抽象性和動態性。傳統的教學手段無法滿足教學的需求,而多媒體技術則具有聲像俱佳、動靜皆宜的特點[7],是傳統教學無法比擬的。多年來我們不斷補充和完善教學手段,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多媒體教學課件。多媒體圖像處理清晰直觀,文字表述簡潔明了、主題突出。課件中的圖像來源于國內外的網絡數據平臺。如講述DNA半保留復制機理時[8],首先將DNA可能存在的幾種復制方式用圖像展現,并利用Meselson和Stahl設計的DNA復制同位素示蹤實驗和密度梯度離心實驗來進行結果驗證,引導學生明確掌握DNA半保留復制特點,并結合文字,通過圖文并茂的多媒體課件,將教學內容中的背景知識、基本概念、基本理論,以及靜態、抽象的微觀知識清晰講解。多媒體課件動靜結合、聲像互動。對于生命過程中動態的知識點,比如DNA的復制、RNA的轉錄、蛋白質的翻譯過程,可以將這些復雜的生命過程利用多媒體手段做成動畫并配以文字和聲像,形象直觀地展現給學生,既加深了學生對知識的理解,也提高了其學習效率。
三、知識領域的拓展
分子生物學的教學內容除包含基礎理論知識外,還有大量理論應用的研究方法部分。我們在教學中不僅僅將知識局限在教材中,利用課堂教學不斷引導學生去了解本學科相關領域內的研究熱點、最新進展、發展趨勢[8],以及生物技術在生產實踐中的廣泛應用。
1.專題講座與專題討論。專題講座是教師根據教學內容,自己組織參考資料對教學內容的延伸與拓展。比如在講授“SNP技術”時,先從遺傳標記分析的發展著手,把一代、二代的標記分析做知識性的回顧,再將納入教材的第三代標記分析“SNP”做詳細的講解,引導大家理解什么是單核苷酸多態性,核苷酸多態性研究的生物學意義以及在醫學、農業、畜牧等多種領域的發展與應用。通過這種方式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和求知欲,也使教師不斷地進行知識的更新,及時了解本學科當前發展的趨勢、研究的熱點以及爭論的問題。專題討論則是以學生為主體,根據課程教學內容,組織學生就某一個專題自行查閱、組織文獻資料,并在課堂上展開討論[9]。比如在講授基因重組的教學內容時,設計“轉基因的利與弊”供學生討論。引導學生思考基因工程藥物和轉基因動植物對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讓知識離開課本走進生活,從而喚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欲望。這不僅使學生更加深入、系統地理解所學知識,并且培養了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10]。
2.生物信息技術與數據庫。生物信息技術已經發展成為分子生物學研究方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如在“PCR技術”的專題講座中,不僅要對實驗目的、原理、操作以及應用進行講解,還要特別對引物設計的生物信息技術進行補充,介紹學生對一些常規的生物信息技術軟件Primer6.0、DNAman、Olig6.0、DNAS-tar、Cluster等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度。在整個分子生物學的教學中,學生需要自行查閱和組織各種文獻資料,因此,必須特別強調互聯網資源運用的重要性。教師通過介紹中國知網、維普、清華同方、NCBI等幾個常用資源庫,使學生了解如何利用資源庫進行查詢,對互聯網資源的熟練應用使學生的知識體系得以完善,學生通過自身的努力來提高信息收集和辨別的能力,培養了學生的自學能力。
四、教學改革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1.教師的專業修養與教學基本功。教師在教學中具有雙重身份,既是一名導演,又是一名演員。作為導演,首先需要有最新的教學理念,整個教學過程中適時設問、適時討論、適時啟發。其次要有較強的課堂組織能力,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把握課堂節奏,調動學生課堂學習激情,使教學有的放矢。否則會在教學中出現“啟而不發”和論證條理不清的現象;作為演員,還要有良好的課程駕馭能力,通過教師扎實的專業知識、廣泛的認知領域、全面的知識結構,呈現給學生的是一個豐盛的知識大餐,而不是一鍋夾生飯。因此作為教師,必須從理論水平、科研水平、思維水平這3個方面提高教師自身的專業素質,此外,還要掌握適合自己的各項教學技能。
2.多媒體教學的合理應用。多媒體教學只是一種提高教學效果的輔助手段,是為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服務的,只有運用合理才可能達到好的效果。因此盡量避免在多媒體教學課件上出現過多的文字,否則多媒體成了教學活動中的主體,老師由照本宣科轉變為扮演放映員和播音員的角色。學生的學習興趣不高,教學效果也就適得其反。多媒體和傳統教學只有合理地結合,取長補短,才能在課堂教學中體現出其真正的價值。總之,教學改革的目標是幫助學生建立學科知識體系,培養學生良好的科學素養,提升學生后繼學習的能力。正如葉圣陶先生所說:“教師的教學,不在于給學生搬去可以致富的金子。而在于給學生點金的指頭。”目前,我們關于分子生物學課堂教學改革還處于不斷探索和實踐階段,除了需要不斷地提高教師自身的學科修養和科研素質外,也以“夯實基礎、拓展知識、增強能力、提高素質”[8]作為教學的目的和人才培養目標,努力在今后把教學工作開展得更加有生有色,為社會培養更多高素質創新型人才。
作者:武曉英 喬宏萍 張猛 吳麗華 郝雪峰 單位:太原師范學院
參考文獻:
[1]朱玉賢,李毅,鄭曉峰,等.現代分子生物學[M].第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
[2]戚曉利,張麗敏,薜春梅.分子生物學教學改革的探索[J].生物學雜志,2003,20(6):51-52.
[3]朱虹.《分子生物學》教學改革的實踐與思考———啟發式教學和論證型教學的綜合運用[J].安徽農學通報,2010,16(1):190-192.
[4]許崇波.《基因工程》課程教學改革初探[J].大連大學學報,2005,26(6):41-43.
[5]文靜,申玉華,趙冰.高等學校分子生物學教學改革初探[J].吉林農業,2013,305(8):92-93.
[6]王榮,劉勇,姜雙林.高等師范院校分子生物學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J].生物學雜志,2012,29(1):100-102.
[7]張金嶺.淺談多媒體教學[J].教育與職業,2009,(30):189-190.
[8]徐啟江,李玉花.分子生物學教學改革與高素質人才培養[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7,158(6):159-161.
第9篇:表觀遺傳學的意義范文
【關鍵詞】 殺傷細胞抑制性受體 基因表達調控 DNA甲基 組蛋白乙酰化
HLA半相合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具有廣泛的臨床應用前景, 但伴隨的問題是移植物抗宿主病發生率高, 免疫重建緩慢, 感染機會增加, 如何克服這些問題是目前造血干細胞移植領域的研究熱點。近年來一系列重要的臨床研究發現, 在去除T細胞的HLA半相合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中, 殺傷細胞免疫球蛋白樣受體(killer cell immnoglobulinlike receptor, KIR)表型不合(移植物抗宿主方向)是對預后有利的因素[1-4]。KIR基因家族是表達在人自然殺傷(nature killer, NK)細胞和部分T細胞表面的具有調節功能的細胞表面分子家族, 它通過與靶細胞表面相應的HLA I類分子結合, 傳導激活或抑制信號, 調節NK細胞功能[5]。KIR基因在NK細胞表面呈隨機性、 多樣性的表達模式, 由此形成了多種多樣的能夠特異性的識別、 清除異常細胞的NK細胞群[6]。因此, 只有了解KIR基因表達調控機制, 才能進一步明確NK細胞的生物學特性, 才能使人為調控NK細胞活性為臨床應用成為可能。但是, 目前關于KIR的表達調控機制尚不完全清楚。本研究旨在從表觀遺傳學的角度對KIR3DL1基因的表達調控機制進行深入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人NK細胞系NK92MI購自美國ATCC細胞庫; 5氮胞苷(5azacytidine, Aza)、 曲古抑菌素A(trichostatin A, TSA)、 肌醇、 巰基乙醇、 葉酸均購自Sigma公司; 氫醌和亞硫酸氫鈉由上海生化試劑公司生產; αMEM培養基、 TRIzol RNA提取試劑盒購自Invitrogen公司; 馬血清、 胎牛血清購自Hyclone公司; DNA提取試劑盒(Wizard Genomic DNA Purification Kit)、 MMLV逆轉錄酶、 dNTPs、 oligo(dT)18、 pGEMT easy載體、 T4 DNA連接酶、 感受態大腸桿菌JM109均購自Promega公司; Taq酶購自TaKaRa公司; PCR產物回收試劑盒(QIAquick Gel Extraction Kit)購自Qiagen公司; PCR引物合成及測序均由北京奧科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完成。
1.2 方法
1.2.1 細胞培養 NK92MI細胞用含2 mmol/L左旋谷氨酰胺、 1.5 g/L NaHCO3、 0.2 mmol/L肌醇、 0.1 mmol/L巰基乙醇、 0.02 mmol/L葉酸、 125 mL/L馬血清、 125 mL/L胎牛血清的αMEM培養基, 于37℃、 50 mL/L CO2飽和濕度條件下培養、 傳代。
1.2.2 總RNA及DNA的提取 采用TRIzol RNA提取試劑盒按說明書步驟提取細胞總RNA, 采用Wizard Genomic DNA Purification Kit按說明書步驟提取細胞基因組DNA, 紫外分光光度計定量。
1.2.3 DNA的亞硫酸氫鹽修飾 參照文獻[7]的方法, 取1 μg經1 mL注射器抽吸剪切后的基因組DNA, 加入去離子水稀釋至50 μL, 向其中加入3 mol/L NaOH 5 μL, 37℃孵育25 min使DNA解開雙鏈; 然后加入新鮮配制的10 mmol/L氫醌30 μL及3 mol/L亞硫酸氫鈉520 μL(其內已加3 mol/L NaOH 370 μL), 混勻后于50℃孵育16 h; 用QIAquick Gel Extraction Kit純化修飾后的DNA, 加入3 mol/L NaOH 5 μL, 37℃孵育20 min終止硫化修飾, 最后經3倍體積的無水乙醇沉淀后溶于20 μL去離子水, 修飾后的DNA于-20℃貯存備用。
1.2.4 PCR擴增及測序檢測啟動子甲基化狀態 按照完全修飾后的KIR3DL1基因DNA序列設計特異性引物, 采用半巢式PCR擴增KIR3DL1基因啟動子。第1輪PCR反應的上游引物: 5′GAAGAAGAGTTTGAATTTTAG3′, 下游引物: 5′CCATATCTTTACCTCCAAATC3′。以經亞硫酸氫鈉修飾后的DNA為模板, 采用25μL的體系行PCR擴增, 體系包含2.5μL 10×PCR緩沖液、 1.5 mmol/L MgCl2、 200 μmol/L dNTPs、 上下游引物各10 pmol/L和1.25 U Taq酶。擴增條件: 95℃預變性10 min, 然后95℃ 90 s, 48℃ 1 min, 72℃ 1 min, 共34個循環, 循環結束后繼續于72℃延伸10 min。將擴增產物經20倍稀釋后取1 μL作為模板進行第2輪擴增, PCR條件同前,上 游引物: 5′GTTAGTATAGATTTTAGGTATTT3′, 下游引物序列同前, 擴增產物長度397 bp。PCR產物行15 g/L瓊脂糖凝膠電泳, 將PCR產物切膠回收后用T4 DNA連接酶與pGEMT Easy載體相連,連接反應體系: PCR產物與pGEMT Easy載體比例為3∶1, 2×連接反應緩沖液 5 μL, T4 DNA連接酶1 μL, 用去離子水補至10 μL, 4℃孵育過夜。取5 μL連接反應產物轉化感受態大腸桿菌JM109, 將PCR初步鑒定陽性的克隆送測序鑒定。
1.2.5 甲基化抑制劑和組蛋白去乙酰化轉移酶抑制劑處理NK92MI細胞 實驗前1 d將NK92MI細胞傳代, 實驗當天將細胞接種在 35 mm細胞培養皿中, 每個培養皿的細胞數為2×106個, 用2 mL完全培養基培養。實驗孔加入終濃度依次為1 μmol/L、 2.5 μmol/L、 5 μmol/L的Aza, 或同時加入2.5 μmol/L的Aza和50 nmol/L的TSA, 或僅加入50 nmol/L的TSA, 對照孔加入等量PBS緩沖液, 細胞繼續置于37℃、 50 mL/L CO2飽和濕度孵箱中培養。每隔24 h更換新鮮培養液及相同濃度的藥物, 于處理72 h后收獲細胞, 檢測基因表達。每組實驗重復3次。
1.2.6 RTPCR檢測KIR3DL1基因表達 在20 μL逆轉錄體系中加3 μg RNA, 42℃水浴1 h, 95℃ 5 min滅活逆轉錄酶后, 取1 μL逆轉錄反應液為模板行PCR擴增。根據文獻[8]合成引物, KIR3DL1上游引物: 5′ACATCGTGGTCACAGGTCC3′, 下游引物: 5′ACAACTTTGGATCTGGGCTT3′, 產物長度為682 bp; 內參照βactin上游引物: 5′CGCGAGAAGATGACCCAGATC3′, 下游引物: 5′TTGCTGATCCACATCTGCTGG3′, 產物長度為734 bp。PCR體系同上。擴增條件: 94℃預變性5 min后, 94℃ 1 min, 61℃ 1 min, 72℃ 45 s, 共5個循環, 然后94℃ 30 s, 60℃ 45 s, 72℃ 45 s, 共30個循環, 循環結束后繼續于72℃延伸10 min。PCR產物行15 g/L瓊脂糖凝膠電泳, 紫外凝膠成像儀掃描分析, 以KIR3DL1/βactin光密度比值作為KIR3DL1 mRNA水平相對值。
1.2.7 統計學處理 數據以x±s表示, 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包行t檢驗, 檢驗水準以P
2 結果
2.1 NK92MI細胞中KIR3DL1啟動子區甲基化模式 CpG二核苷酸在KIR基因轉錄起始區域密度增加, 其出現率(觀測值與期望值的比率)≥0.6, 符合CpG島的定義[9], 因此, 本研究將KIR3DL1基因自轉錄起始位點上游-270 bp至下游+69 bp之間的這段長339 bp的序列定義為CpG島, 為便于分析說明, 將這段序列內的全部19個CpG二核苷酸位點以轉錄起始位點編號, 上游為“-”, 下游為“+”。NK92MI細胞基因組DNA經亞硫酸氫鹽修飾后, 采用PCR擴增KIR3DL1基因啟動子序列, 將擴增產物連接到T載體, 轉化感受態大腸桿菌, PCR初步鑒定陽性重組子, 隨機挑取10個克隆行初步PCR鑒定, 均可擴增出與預期大小相一致的目的片段(圖1)。陽性克隆進一步測序, 結果與GenBank數據庫中KIR3DL1基因啟動子序列(基因號NM_013289)比對, 除第1、 4、 5號克隆序列錯誤外, 得到7條正確的序列。亞硫酸氫鹽修飾可以使DNA中未發生甲基化的胞嘧啶脫氨基轉變成尿嘧啶, 而甲基化的胞嘧啶保持不變, 以第10號克隆測序結果為例, 可見全部19個CpG二核苷酸位點由于被甲基化, CpG二核苷酸中的胞嘧啶保持不變, 其他部位的“C”全部發生改變(圖2)。綜合分析所得7條正確序列測序結果, NK92MI細胞中KIR3DL1基因啟動子CpG二核苷酸位點甲基化頻率在70%~100%之間, 因此, KIR3DL1基因啟動子處于高度甲基化狀態(圖3)。
圖1PCR方法鑒定含KIR3DL1啟動子pGEMT easy載體的克隆(略)
Fig 1 Identification of clones containing KIR3DL1 promoterpGEMT easy vector by PCR amplification
M: DNA marker; 1-10: PCR products of clone 1 to 10.
圖2 經硫化修飾后的KIR3DL1啟動子部分測序結果(略)
Fig 2 Partial result of DNA sequencing of bisulfiteconverted KIR3DL1 promoter
圖3 NK92MI細胞系中KIR3DL1啟動子各CpG位點的甲基化頻率(略)
Fig 3 Methylation frequency at inpidual CpG positions of KIR3DL1 promoter in NK92MI cell line
2.2 去甲基化誘導NK92MI細胞KIR3DL1表達增加 為進一步分析KIR3DL1基因啟動子甲基化與基因表達的關系, 采用不同濃度的去甲基化藥物Aza處理NK92MI細胞, 結果顯示, 終濃度為1 μmol/L的Aza作用72 h, NK92MI細胞中KIR3DL1 mRNA表達量與對照組相比無明顯增加(t=0.632, P=0.562), 而2.5 μmol/L和5 μmol/L的Aza可以使KIR3DL1 mRNA表達量與對照組相比分別增加66.6%和114.6%(統計分析結果分別為: t=3.411, P=0.027; t=6.454, P=0.003), 說明去甲基化藥物Aza可以誘導NK92MI細胞中KIR3DL1表達, 隨藥物濃度增加, 這一誘導作用逐漸增強(圖4A); 單用50 nmol/L的TSA處理NK92MI細胞72 h, KIR3DL1 mRNA表達量與對照組相比無統計學意義(t=0.203, P=0.852), 將50 nmol/L的TSA與2.5 μmol/L Aza聯用處理NK92MI細胞72 h, KIR3DL1 mRNA表達量與單用Aza組相比也無統計學意義(t=1.840, P=0.140), 說明單用TSA不能誘導KIR3DL1表達, 其與Aza聯用后也沒有協同作用(圖4B)。
圖4 RTPCR方法檢測經5氮胞苷和曲古抑菌素A處理的NK92MI細胞中KIR3DL1 mRNA表達(略)
Fig 4 Detection of KIR3DL1 mRNA levels in 5azacytidine and trichostatin Atreated NK92MI cells by RTPCR
A: NK92MI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final concentrations of 5azacytidine (1 μmol/L, 2.5 μmol/L and 5 μmol/L) for 72 h; B: NK92MI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2.5 μmol/L of 5azacytidine and (or) 50 nmol/L of trichostatin A for 72 h. aP
3 討論
KIR基因家族位于人染色體19q13.4, 目前發現有17個成員。KIR基因家族的特點是各成員在NK細胞表面呈隨機性、 多樣性的表達, 每個NK細胞只表達KIR基因家族部分成員, 一種KIR分子的表達不依賴于其他KIR分子, 從而形成了表達多種多樣KIR分子的NK細胞群[5]。KIR基因的這一特有的表達模式對NK細胞特異性識別和清除異常細胞非常重要。在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中由于供受者之間KIR不相容引發的異源反應性NK細胞活性有利于增強移植物抗白血病作用、 抑制移植物被排斥和移植物抗宿主病、 促進造血干細胞植入, 延長患者生存期, 因此, 明確KIR表達調控機制, 調節NK細胞活性, 對改善造血干細胞移植預后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KIR基因表達調控機制已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10]。KIR3DL1基因與KIR家族其他成員的5′側翼區序列同源性高達91.1%~99.6%, 在NK細胞表面呈多樣性表達[11]。本研究組的前期實驗證實KIR3DL1基因啟動子在沒有內源性KIR3DL1基因表達的K562細胞中具有活性(結果未顯示); Stewart等[12]的研究也證實, KIR3DL1基因啟動子不僅在有KIR3DL1基因表達的NK細胞系YTIndy中有活性, 并且在沒有KIR3DL1基因表達的T細胞系Jurkat中也具有活性。可見KIR3DL1基因轉錄激活所需的反式作用因子在不同細胞系中廣泛分布, 提示表觀遺傳機制可能在調控KIR3DL1基因表達中發揮重要作用。為此, 本研究首先采用亞硫酸氫鹽測序法對NK92MI細胞中KIR3DL1基因啟動子甲基化狀態進行了檢測, 證實KIR3DL1基因啟動子存在高甲基化, 然后用去甲基化藥物處理NK92MI細胞, 研究啟動子甲基化與KIR3DL1基因表達的關系, 以確定KIR3DL1基因的表達是否受甲基化調控。
大量研究已證實DNA甲基化可以調控基因表達[13], 啟動子甲基化, 基因轉錄活性被抑制; 去甲基化, 這一抑制作用被取消。DNA甲基化介導轉錄抑制的機制可能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 DNA甲基化直接干擾特異轉錄因子與各自啟動子的識別位點相結合, 抑制基因轉錄; 其二, 通過在甲基化DNA上結合特異的轉錄阻遏物(如甲基胞嘧啶結合蛋白1, 2), 這種蛋白質可以和轉錄因子競爭性地與甲基化DNA的結合位點結合, 抑制基因轉錄; 其三, 甲基化改變了蛋白質與DNA的相互作用, 導致染色質結構的改變,抑制基因轉錄。Aza是一種常用的甲基化抑制劑, 它通過與DNA甲基化酶共價結合, 降低其生物活性,從而逆轉DNA甲基化。本研究證實Aza能夠誘導NK92MI細胞KIR3DL1基因表達增加, 由此可以推斷KIR3DL1基因表達受啟動子甲基化調控。
組蛋白乙酰化是表觀遺傳調控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14], 組蛋白乙酰化由乙酰基轉移酶催化完成, 此時染色質呈疏松狀態, 有利于基因的表達; 相反, 組蛋白去乙酰化由去乙酰基轉移酶催化完成, 此時染色質呈壓縮狀態, 不利于基因的表達。組蛋白去乙酰化轉移酶抑制劑TSA通過提高組蛋白乙酰化水平, 活化基因轉錄。但本研究應用TSA處理NK92MI細胞, 未見KIR3DL1基因表達增加, 也沒有觀察到其與Aza的協同作用; 本研究的前期結果顯示, 即使用300 nmol/L的TSA也不能明顯增加KIR3DL1基因轉錄(結果未顯示); Santourlidis等[15]的研究也發現, 用25 nmol/L的TSA處理NKL細胞系不能誘導KIR3DL1基因轉錄增加。由此推測組蛋白乙酰化可能在KIR3DL1基因表達調控中作用不大。
綜上所述, 通過檢測NK92MI細胞KIR3DL1基因啟動子區甲基化模式, 證實NK92MI細胞中KIR3DL1基因啟動子存在高甲基化, 去甲基化處理能夠誘導NK92MI細胞表達KIR3DL1基因, 因此, NK92MI細胞中KIR3DL1基因表達受啟動子甲基化調控。
參考文獻
[1] Bethge WA, Haegele M, Faul C, et al. Haploidentical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adults with 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ing and CD3/CD19 depletion: fast engraftment and low toxicity[J]. Exp Hematol, 2006, 34(12): 1746-1752.
[2] Ruggeri L, Capanni M, Casucci M, et al. Role of natural killer cell alloreactivity in HLAmismatche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Blood, 1999, 94(1): 333-339.
[3] Ruggeri L, Mancusi A, Burchielli E, et al. Natural killer cell recognition of missing self and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transplantation[J]. Semin Cancer Biol, 2006, 16(5): 404-411.
[4] Ruggeri L, Mancusi A, Capanni M, et al. Donor natural killer cell allorecognition of missing self in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transplantation fo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hallenging its predictive value[J]. Blood, 2007, 110(1): 433-440.
[5] Husain Z, Alper CA, Yunis EJ, et al. Complex expression of natural killer receptor genes in single natural killer cells[J]. Immunology, 2002, 106(3): 373-380.
[6] Marsh SG, Parham P, Dupont B, et al. Killercell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KIR) nomenclature report, 2002[J]. Eur J Immunogenet, 2003, 30(3): 229-234.
[7] Frommer M, McDonald LE, Millar DS, et al. A genomic sequencing protocol that yields a positive display of 5methylcytosine residues in inpidual DNA strands[J]. Proc Nati Acad Sci USA, 1992, 89(5): 1827-1831.
[8] Thompson A, van der Slik AR, Koning F, et al. An improved RTPCR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killercell immunoglobulinlike receptor (KIR) transcripts[J]. Immunogenetics, 2006, 58(11): 865-872.
[9] GardinerGarden M, Frommer M. CpG islands in vertebrate genomes[J]. Mol Biol, 1987, 196(2): 261-282.
[10] 高曉寧, 于 力. NK細胞KIR基因表達調控機制研究進展[J]. 國際輸血及血液學雜志, 2007, 30(2): 157-159.
[11] van Bergen J, Stewart CA, van den Elsen PJ, et al.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moters of independently expressed killer cell Iglike receptors[J]. Eur J Immunol, 2005, 35(7): 2191-2199.
[12] Stewart CA, van Bergen J, Trowsdale J. Different and pergent regulation of the KIR2DL4 and KIR3DL1 promoters[J]. J Immunol, 2003, 170(12): 6073-6081.
[13] Jones PA, Takai D. The role of DNA methylation in mammalian epigenetics[J]. Science, 2001, 293(5532): 1068-1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