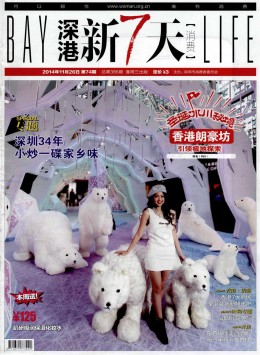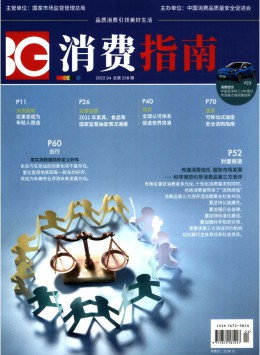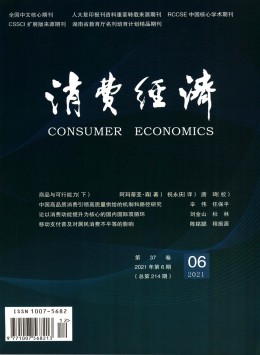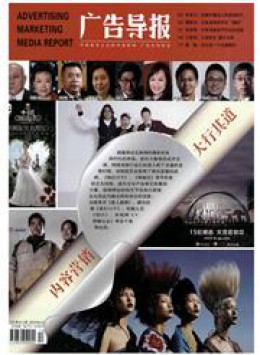消費心理下偏好與習性營銷策略探索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消費心理下偏好與習性營銷策略探索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十三五”時期,關于文化生產與消費、文旅融合與文旅消費的研究熱度很高。進入“十四五”時期,相關研究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借鑒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可以推論出:文化消費心理偏好依托于特定的心理習性。進一步可以發現:文化消費心理習性導致文化消費習慣形成,通過誘導消費者的文化消費心理,可以對拉動文化消費、擴大內需發揮現實作用。因此,對文化消費心理偏好與習性探析,具有學術與應用價值。然而,文化消費心理的專項研究還相對匱乏,亟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一、“文化消費”已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
盡管消費心理學在國內外都有廣泛的研究,國外自19世紀末開始建構理論體系,現已較為成熟,且不斷拓展著學科視野,不斷產生新的理論;國內自20世紀末相關理論漸豐,現在其已經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然而,文化消費心理學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既有的研究都很少。國外學界尚未有專門探討文化消費和文化消費心理的研究,往往是從消費的文化心理角度來研究問題,并常常把時尚消費、傳媒消費、品牌消費等混同于文化消費。而在國內學界,伴隨著2000年以來文化產業研究成為熱點,文化消費研究逐漸升溫,尤其是從“十二五”時期開始,國家層面引導和擴大文化消費的相關政策法規不斷出臺,各地紛紛啟動拉動文化消費試點項目,致使學界自然而然關注到了“文化消費”這一新的學術增長點。
二、文化消費心理偏好依托于特定的心理習性
消費偏好(ConsumerPreference)又稱“消費者嗜好”,反映消費者對于所購買商品的主觀評價。(林百鵬,臧旭恒主編.消費經濟學大辭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268-269.)這種偏好是一種主觀傾向,反映了一種心理定勢。短期看,消費偏好一般是穩定的,如商品價格上漲會直接削弱一部分有廉價商品消費偏好的消費意愿;而長期看,卻是會改變的。消費偏好的變化和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主要有經濟、社會、文化、地理、生活等因素。經濟因素如國家經濟狀況和個人經濟能力,對于消費偏好形成有著重要作用;社會因素如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通常會導致消費者對非必需商品的消費偏好發生波動;文化因素即消費者所處的“文化語境”,包括文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風俗習慣、傳統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等,會對消費者的選擇造成顯著影響;地理因素如我國人民“南甜、北咸、東辣、西酸”的飲食消費偏好,就是地理環境所致;生活因素如一個人婚前婚后以及有孩子時,消費偏好往往是截然不同的。文化消費偏好主要體現為以下幾種:第一,文化價值觀認同偏好,如有些人偏好消費美國傾銷的所謂“普世價值”文化產品,有些人則頗喜欣賞我國的“主旋律”文化產品。第二,文化類型偏好,宏觀上包括對于東西方文化、傳統與現代文化、大眾與精英文化的不同偏好,如有些人偏好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等;微觀上包括對于文化題材、文化內容等的偏好,如有些人偏好英雄題材、玄幻內容等。第三,文化審美偏好,即對于文化產品形式風格方面的偏好,如有些人對于古風風格的文化產品情有獨鐘,有些人特別喜歡具有民族元素、民族風情的文化產品。第四,文化品牌偏好,如有些人是迪士尼、夢工廠動畫片的忠實“粉絲”。由于文化消費的訴求不在于物質載體,文化消費是脫物化的消費,因而文化消費心理偏好和物質消費心理偏好的成因有所不同,更為主觀化、個性化、抽象化,也更加復雜。筆者借鑒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推論出:文化消費心理偏好依托于特定的心理習性(慣習)。布爾迪厄所說的第一種形態(身體形態)的文化資本即反映為習性(慣習)。而其提出的“習性(慣習)”概念是一個結構性概念,習性(慣習)是“被建構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和“建構中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成為一個被牢固鑄造的結構,是“結構的結構”,“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釋力”(余乃忠,陳志良.習性:“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釋力”———布爾迪厄建構的結構主義神話[J].現代哲學,2009〈01〉:35-39.),推動了一系列結構的再生產:個體結構再生產,指個體習性(慣習)結構的再生產,通俗地說就是性情、人格結構的再生產;社會結構再生產,指權力結構、階級結構和社會資源分配結構的再生產;文化結構再生產,尤指文化特權結構的再生產———造就了個體間的區分、社會階層的區分和社會文化的區分。并且,“習性(慣習)”這一概念本身帶有很強的文化特質和文化語意,布爾迪厄本人曾說,“‘文化’可能是比‘習性(慣習)’更好的術語。但是,這個過分被決定的術語帶有被誤解的危險,而且不容易界定其有效性的條件。”(包亞明.布爾迪厄文化社會學初探[J].社會科學,1997〈04〉:70-73.)因此他便退而求其次地選擇了“習性(慣習)”這一突出主體主觀性和控制性的術語,以突出社會場域中行動主體的“實踐感”。由此可知:習性(慣習)根本上是一種社會文化結構在個體層面的反映,個體的心理習性(慣習)就是一種文化習性(慣習)。依據布爾迪厄的理論,可以認為:特定的心理習性(慣習)是導致特定的文化消費心理偏好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因為習性(慣習)本身就是一種結構化的主體傾向系統,本身就包含著心理偏好,決定了行為偏好。舉例而言:一個在西方國家學習生活多年的人即便回國,其被西化的習性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在文化消費方面,其一般會更偏好消費具有西方價值和西式風格的文化產品。同樣的,“習性(慣習)”這一反映第一種形態的文化資本的概念,能夠很好地解釋處于不同社會階層消費者的文化消費偏好存在差異的原因,比如:中產階級和農民工由于經濟基礎和文化習性不同,文化消費偏好會有不同。
三、文化消費心理習性導致文化消費習慣形成
消費習慣(ConsumerHabit)指消費者在一定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長期培養形成的,以一定的消費心理為基礎的消費行為模式。對于某些商家、品牌的商品形成了某種消費習慣的消費者,往往不加挑選、不加比較地持續進行消費。以文化消費為例:習慣于使用某品牌某平臺(如得到、知乎、分答、喜馬拉雅FM、蜻蜓FM、酷狗音樂、網易云音樂等)知識付費、內容付費、娛樂付費功能的消費者,往往會一直使用下去,因為對于平臺的服務、操作熟悉,使用順手。根據消費者范圍的不同,消費習慣有大小范圍之分。大范圍的消費習慣即群體消費習慣,如由不同年齡段的消費者所構成的具有代際文化差異的消費習慣,由不同地域的人口所構成的具有地理和氣候差異、地方文化差異的消費習慣,由不同民族的消費者所構成的具有民族文化差異、民族性格差異的消費習慣等。小范圍的消費習慣即個體消費習慣,除了由不同消費個體所構成的具有個性差異的消費習慣之外,由于家庭是小型的社會組織單位,因而還應包括由不同家庭所構成的具有家庭文化差異、家庭性格差異、家庭稟賦差異的消費習慣。而根據定型程度和對人造成影響的程度強弱,還可以劃分出“可變性大”和“可變性小”的兩種相對而言的消費習慣類型。前者常常隨著生活環境、周圍人群、個人際遇的改變而改變,比如“入鄉隨俗”“隨大流”“此一時,彼一時”等;后者則根深蒂固,甚至具有代際傳承性,無論周遭境遇如何、客觀條件如何改變,都會長期地、穩定地甚至一代代地延續下去。大多關于消費心理學的研究都將消費偏好和消費習慣相提并論,認為偏好導致習慣形成,或者將兩者等同,認為習慣就是偏好。在此,筆者對這兩個概念進行鑒別區分,認為消費習慣是行為層面的,而消費偏好是心理層面的,行為習慣基于心理偏好,是心理偏好的外化表現和模式化定型。上文闡明了文化消費心理偏好成因和物質消費有所不同,依托于特定的心理習性(慣習),或言文化習性(慣習),因而可以推出:文化消費習慣成因也和物質消費有所不同,也是由習性(慣習)所致。布爾迪厄社會學理論中的關鍵詞“習性(慣習)”并不是人們常說的“習慣”,雖然兩個詞在英語中都是“Habit”,但是我國翻譯者卻精心區別了兩者。翻譯過來的“習性(慣習)”是一個頗顯深奧的術語。“習性(慣習)”側重于心理層面,是一種固化的性情,形成于特定的社會場域中(如法律、宗教、政治、文化、美學、教育等場域),有著深刻的、分別的(“區分”的)、主體特色(個性)鮮明的文化烙印,是特定場域結構和所生成的特定文化心理結構的結構化(固化);“習慣”側重于生理層面,是某種定型的行為,這個詞說明了某種行為的機械重復性,強調慣性和惰性,不能反映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主體的心理傾向,也無法對應特定的社會場域,不具備結構性。這樣看來,就可以理解作為“結構再生產”之鑰的習性是“席卷一切的”,結構化(心理結構化)的內在習性決定了外在習慣,所以,文化消費習慣是文化消費心理習性(屬于文化心理習性)由內而外的反應。四、當代文化產業經營主體可實施的營銷心理策略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并非生而有之和一成不變的,而是具有可誘導性和可變性的。文化消費心理既然是消費心理的一種,當然也是可以誘導的。因此,文化產業經營主體可實施營銷心理策略。第一,運用大數據技術精準讀心。大數據技術實現了對于潛在消費需求精準挖掘、對于目標消費者精準定位、對于商品信息和廣告等精準投放、對于信息投放效果精準評估、對于未來消費趨勢精準研判等一系列精準營銷的可能性。(倪寧,金韶.大數據時代的精準廣告及其傳播策略———基于場域理論視角[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4,36〈02〉:99-104.)從根本上看,這一切都建立在大數據技術“精準讀心”的基礎上,即通過海量數據的自動化統計分析消費行為軌跡,消費者的消費心理被全方位解讀。在這樣的技術環境下,傳統的“人找貨”消費模式逐漸被顛覆,新型的“貨找人”消費模式事實上促進了供求精準對接。今天,文化產業領域已經廣泛地運用大數據技術精準解讀消費心理和預測消費行為。然而,當前的“數據讀心術”尚不夠深入,深度透析能力還有待提升;而隨之而來的“算法推送術”也因缺乏人為干預、缺乏主流價值觀介入和引導,導致文化消費領域產生一些亂象,如不雅視頻被高頻推送和高頻點播等,因此對數據技術使用建立規則至關重要。第二,產品創意設計要精準攻心。文化產品創意設計的根本在于符號建構和意義表征,所建構的符號事實上映射著目標消費者的內心世界,表征著目標消費者所認同的文化意義。因而,創意設計的“精準攻心”環節,主要就是使得文化形式和內容對應上文所論述的幾種主要的文化消費心理模式,即從眾求同式、標新立異式、陪伴需要式、自我陶醉式、情感養成式、美化生活式、裝點“面子”式、夢想寄托式、超越現實式等。第三,注重情感導入以精準貼心。文化產品和物質產品很大的一點區別,在于文化產品具有豐富的情感內涵和生動的情感交互功能,其本身傳達著某些情感,而消費者往往還能賦予其額外的情感,消費過程往往是一個情感投入和情感共鳴的過程,如閱讀小說、看電影等,讀者和觀眾通常都有和書中人、劇中人“同悲喜、共命運”的情感體驗。因而,文化產業經營者要善于利用文化產品本身具有情感言說的優勢,更加注重貼合消費者內心的情感需求。第四,文化價值觀言說要深入人心。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背景下,使得某種文化價值觀深入人心的前提是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前,文化消費領域存在主流文化價值觀言說相對無力,和當代消費者的文化消費心理存在隔閡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政府要發揮好宏觀調控職能,宣傳文化部門要把文化產業經營者(而非一般大眾)作為關鍵對象加以引導。第五,提升供給品質以長效走心。與美、英、法、日、韓等文化產業強國相比,我國的文化供給品質尚存差距。比如,影視產品視覺技術還不夠先進,特效效果不夠震撼;旅游景區打造模式粗放低端,尚未打造出像是“迪士尼樂園”這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旅游品牌;AI技術在文化創意領域應用還不夠廣泛等。盡管大多數文化產品不是功能性產品,并不存在功能性產品的質量問題,但仍舊存在內容品質問題,一者關乎“品”,即品位、品格(格調)等問題;二者關乎“質”,如視聽類產品的畫質、音質、播放流暢度等。文化供給不但要“創意為核”,還要“品質為王”,才能鎖定消費者,才能“長效走心”,使消費者持續消費。
作者:徐望 單位:江蘇省文化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