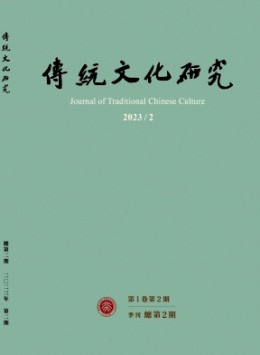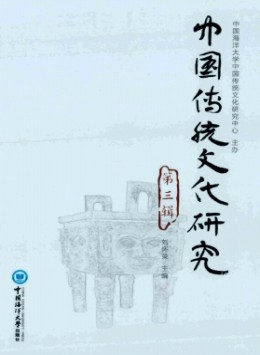傳統(tǒng)音樂論文:傳統(tǒng)音樂文化理論思考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傳統(tǒng)音樂論文:傳統(tǒng)音樂文化理論思考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作者:1陳 柳 2吳姝嵐 3胡曉東 單位:1 2江西省上饒師范學(xué)院 3西南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
對于多數(shù)青年學(xué)者而言,要實(shí)現(xiàn)這個(gè)跨越并非易事,它不僅需要有跳出音樂小文化圈進(jìn)入國家歷史大文化的宏觀學(xué)術(shù)視野,更要有扎實(shí)的文獻(xiàn)功底和不畏艱苦深入實(shí)地考察的學(xué)術(shù)勇氣。項(xiàng)先生呈現(xiàn)給我們的,其實(shí)就是歷史的民族音樂學(xué)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產(chǎn)生的學(xué)術(shù)意義異常深遠(yuǎn)。
首先,它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或當(dāng)下的各種音樂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專著《山西樂戶研究》中,項(xiàng)先生給學(xué)界提供了一種在宏觀把握下的微觀研究,歷時(shí)性與共時(shí)性相結(jié)合的研究,跨學(xué)科研究與集體性協(xié)同攻關(guān)研究等幾種方法相聯(lián)合的研究模式。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為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更加有效的途徑,給后學(xué)以較大的開示。樂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體,歷時(shí)一千數(shù)百年,其間必然形成體系化,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影響也必然是深遠(yuǎn)的。但遺憾的是,以往乃至當(dāng)代的史家對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樂戶研究》通過對樂戶的源流、歷史分布、組織形式和文化形態(tài)、音樂文化特征以及樂戶對音樂文化傳統(tǒng)的貢獻(xiàn)等幾個(gè)方面的考證,揭示出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在大一統(tǒng)的封建樂籍制度背景下有序傳承的歷史脈絡(luò)。作者找到了這種制度化傳承的有效方式——輪值輪訓(xùn)制,并對它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闡述。[2]而作者的獨(dú)到之處就在于綜合運(yùn)用了社會學(xué)、民族音樂學(xué)、民俗學(xué)、歷史學(xué)、考古學(xué)等多學(xué)科方法進(jìn)行全方位的解讀與剖析。
項(xiàng)先生曾多次在各種學(xué)術(shù)場合倡導(dǎo),要高度重視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傳承中這種嚴(yán)密的制度化的傳播方式。我們過去想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民間音樂是由勞動人民世世代代口傳心授傳承下來的,并且這種方式是自然的、無序的。其實(shí)不然,一千數(shù)百年的樂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傳承方式,例如宮廷教坊、府縣教坊、府州散樂、衙前樂營等等,才是我國傳統(tǒng)音樂傳承之主脈。這種傳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沒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間音樂悄然接衍,在民間音樂文化中存活。因此,樂籍制度下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傳承,好比浩瀚無際的民間音樂大海深處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著這一理念,項(xiàng)先生繼續(xù)深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論文,如《輪值輪訓(xùn)制——中國傳統(tǒng)音樂主脈傳承之所在》(《中國音樂學(xué)》2001年第2期第11-20頁)、《論制度與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關(guān)系——兼論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音樂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頁)、《北周滅佛‘后遺癥’——再論音聲供養(yǎng)與音聲法事的合一》(《文藝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頁)、《從<朝天子>管窺禮樂傳統(tǒng)的一致性存在》(《中國音樂》2008年第1期第33-42頁)、《關(guān)注明代王府的音樂文化》(《音樂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頁)、《傳統(tǒng)音樂的個(gè)案調(diào)查與宏觀把握——關(guān)于‘歷史的民族音樂學(xué)’》(《中國音樂》2008年第4期第1-7頁)、《小祀樂用教坊——明代吉禮用樂新類型(上、下)》(《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年第3期第25-35頁、第4期第55-76頁)等等,都屬于這方面的研究。然而,縱觀整個(gè)音樂學(xué)界,對于樂籍制度與傳統(tǒng)音樂文化傳承的研究仍剛剛起步,有待于更多學(xué)者參與進(jìn)來,做更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們科學(xué)把握音樂小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大文化之間相輔相成的血肉聯(lián)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內(nèi)在邏輯而孤立地看問題。例如,在中國傳統(tǒng)禮樂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樂史學(xué)家們往往多注重“樂”之形態(tài)——音樂本體,而忽略樂與禮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和功能作用。回過頭來,文史學(xué)者在談及傳統(tǒng)禮樂文化時(shí)又往往只關(guān)注“禮”的含義與范疇,而對于與“禮”相輔相成、相須為用的“樂”卻淺嘗輒止或干脆避而不談。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雙方學(xué)者的知識背景使然,還有一個(gè)深層次的緣由就是學(xué)者們的專業(yè)本位觀的影響。基于此,項(xiàng)先生提出一種從“制度、樂人與音樂本體相結(jié)合”的新的研究視角,使人們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有了全新的認(rèn)識和理解。
“以樂觀禮”,就是在這種學(xué)術(shù)理念下導(dǎo)引出來的次生概念。項(xiàng)先生認(rèn)為,必須將歷史上各個(gè)時(shí)期的國家禮制(三禮五禮)與樂的對應(yīng)、演化與等級關(guān)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義。只有將國家典章制度下的禮樂樂隊(duì)組合、不同場合與不同禮制的關(guān)系搞清楚,才能夠真正理解禮樂文化的功能性內(nèi)涵;只有將雅與俗、雅樂與禮樂的關(guān)系加以辨析,并明確各類禮樂的使用范圍,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禮樂籠統(tǒng)論之。
“以樂觀禮”,只有對禮中用樂的等級觀念有深層把握,明了同一種禮制,哪些等級能夠用樂?明了禮制本身的差異性,才能夠看清楚樂之于禮的嚴(yán)肅性和豐富性;只有對國家禮樂如何轉(zhuǎn)化為民間禮俗用樂的過程作出梳理,并對當(dāng)下民間禮俗如何承載、接衍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國家禮樂作出合理判斷,才能夠?qū)Ξ?dāng)下全國各地廣泛存在的傳統(tǒng)用樂形式、不同樂隊(duì)組合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以及相當(dāng)數(shù)量樂曲的屬性作出合理的解釋。對歷史上國家禮樂承載群體的整體把握是認(rèn)知“以樂觀禮”的關(guān)鍵之一,南北朝以降樂籍制度的存在對于國家禮樂實(shí)施的作用是絕對不可以忽略的。對上述問題均需鉤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則,這種論禮樂而混沌的狀況將永遠(yuǎn)無法得到徹底的改觀。[4]
換言之,只有對封建禮制的功能與本質(zhì),禮與樂對應(yīng)的內(nèi)在意涵和互文關(guān)系[5]有正確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聯(lián)系的理念,全面客觀地認(rèn)知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傳統(tǒng)音樂文化事像中的某一個(gè)案和音樂品種。
此外,在論及古代禮樂制度與各音樂形態(tài)的意涵與互通方面,項(xiàng)先生論述頗多,如《當(dāng)下傳統(tǒng)音樂與民間禮俗的依附與共生現(xiàn)象》(《音樂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頁)、《禮樂•雅樂•鼓吹樂之辨析》(《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0年第1期第3-12頁)、《中國音樂文化的‘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6年第1期第3-10頁)、《以<太常續(xù)考>為個(gè)案的吉禮雅樂解讀》(《黃鐘》2010年第3期第99-112頁)等,皆屬于這一學(xué)術(shù)論域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學(xué)術(shù)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寬本學(xué)科的研究領(lǐng)域,夯實(shí)本學(xué)科的研究基礎(chǔ),推動本學(xué)科的健康發(fā)展。一門學(xué)科欲獲得全面發(fā)展,需要有一個(gè)艱難的歷時(shí)性過程,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學(xué)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間肯定會面臨新舊觀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擇與揚(yáng)棄。音樂學(xué)學(xué)科的發(fā)展,必須引入他學(xué)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論,以更新和壯大自己的學(xué)術(shù)生命。
以音樂史學(xué)為例,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距今已逾半個(gè)多世紀(jì)了,近三十年來,我國音樂史學(xué)界無論在研究理念還是具體的方法論上都實(shí)現(xiàn)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當(dāng)“傳統(tǒng)遭遇現(xiàn)代”,當(dāng)原有的研究結(jié)論與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當(dāng)傳統(tǒng)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經(jīng)無法把握愈來愈多的學(xué)術(shù)事像,無法對新生的學(xué)術(shù)難題[6]作出合理的闡釋時(shí),我們該如何抉擇?正如項(xiàng)先生在《由音樂歷史分期引發(fā)的相關(guān)思考》一文(《音樂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頁)中指出的那樣,音樂史學(xué)在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多學(xué)科視角的理念增強(qiáng),從而導(dǎo)致了對本學(xué)科發(fā)展的重新審視,特別是考古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地理學(xué)、文化人類學(xué)、社會學(xué)、民族學(xué)、民俗學(xué)等學(xué)科對音樂史學(xué)發(fā)展的貢獻(xiàn)尤甚。接著,作者談到關(guān)于“重寫音樂史”的話題,認(rèn)為既有的音樂史學(xué)論域只是將音樂作為審美、欣賞的意義,而弱化了中國歷史上音樂既有的社會功能性和實(shí)用功能性的豐富內(nèi)涵。如此則很難反映中國音樂在歷史語境下的整體樣貌,諸如音樂的存在方式、國家禮樂的上下貫通、民間對于國家禮制中吉禮理念與國家禮樂中禮儀用樂的重新組合與拼裝、在“為神奏樂”理念下相當(dāng)古老的音樂形態(tài)可能近乎原樣承繼于當(dāng)下。項(xiàng)先生建議從社會整體把握的視角,以國家禮制下的多功能性用樂為主線寫出一部中國音樂文化史——國家樂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禮樂文化史。認(rèn)為對樂籍制度和制度下群體承載的探研,應(yīng)該成為一個(gè)相對長歷史時(shí)期音樂史學(xué)把握的重點(diǎn)。
在此理念下,才能夠認(rèn)知傳統(tǒng)社會中主導(dǎo)層面制度下創(chuàng)樂和用樂的整體一致性和體系化,繼而看到在這種一致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動態(tài)延展性和差異性。項(xiàng)先生指出,目前這項(xiàng)工作已經(jīng)展開,并呼吁廣大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
此外,項(xiàng)先生的《樂籍制度的畸變期考述》(《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1年第4期第35-43頁)、《音樂史學(xué)與民族音樂學(xué)論域的交叉》(《新疆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3年第1期第64-69頁)、《功能性•制度•禮俗•兩條脈——對于中國音樂文化史的認(rèn)知》(《中國音樂》2007年第2期第25-34頁)、《傳統(tǒng)音樂文化研究的跨學(xué)科溝通問題》(《人民音樂》2010年第3期第74-77頁)等論文都對音樂史學(xué)學(xué)科建設(shè)的諸多新問題進(jìn)行了深度的思考與論述。
與項(xiàng)先生稍熟識的學(xué)者都知道,這幾年,他的學(xué)術(shù)理念在不斷地更新拓寬,研究厚度亦在不斷地鑿深。究竟是什么力量給了他持續(xù)激活學(xué)術(shù)火花的源動力呢?那就是與人類學(xué)、社會學(xué)、史學(xué)等大學(xué)術(shù)界的接通,正如項(xiàng)先生那句振聾發(fā)聵般的倡導(dǎo)和呼吁:“音樂史學(xué)走出書齋,傳統(tǒng)音樂接通歷史,加強(qiáng)與大學(xué)術(shù)界的溝通與合作!”這就是所謂“接通”的意義,至今,已沒有任何一門學(xué)科可以拒絕多學(xué)科交叉互融的選擇。唯有不斷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思維框式,以寬容的學(xué)術(shù)胸懷接引最新的學(xué)科理念和研究方法,學(xué)術(shù)研究才能長久常新。“問泉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項(xiàng)先生正是以開放的學(xué)術(shù)視野吸納多學(xué)科的源頭活水,終匯成一股清新的浪潮,時(shí)時(shí)保持鮮活的研究理念和旺盛的開拓態(tài)勢。作為在學(xué)術(shù)上剛剛起步的青年學(xué)人,更應(yīng)該謹(jǐn)記這一點(diǎn),需時(shí)時(shí)檢驗(yàn)自己在研究工作中的理念和方法論是否已經(jīng)陳舊或南轅北轍,不得要領(lǐng)?